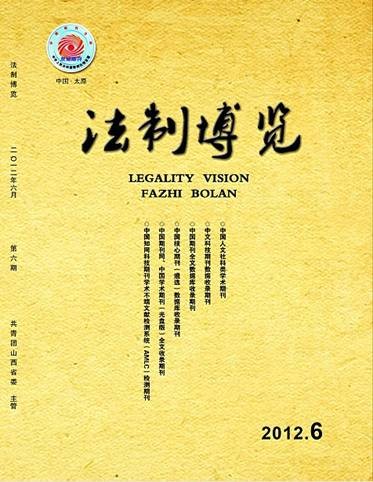新闻资讯
简介: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种新的司法标准?
自2011年在德国汉诺威贸易展上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参考 Kagermann、Lukas 和 WahlsterKagermann 等人,2011),关于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讨论一直由“4.0”概念主导(参考普法伊弗菲佛,2017)。虽然“工业 4.0”指的是特定的生产模式和四个相关的技术飞跃(从蒸汽机到电气化、信息时代和当今的网络物理系统),但德国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创造了“Arbeit”一词4.0'(英国医学会,2015:34-35)指的是工作形式和机构的转变。这里讨论的四个阶段是:(1.0)十八世纪末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人协会的出现,(2.0)大规模生产和福利国家的开始,(3.0)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市场经济,以及(4.0)基于互联网的工作以及相关的社会妥协和价值转移。1.0 至 3.0 阶段以有酬就业制度为标志;即使在今天,有偿工作也主要由在实体(商业)组织内持有永久雇佣合同的雇员进行。所有形式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事故、失业还是退休)——最终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就业模式。
尽管如此,众包工作还是打破了这种模式:像大多数平台精心策划的工作组织模式一样,众包工作经常绕过就业法规,从而破坏传统劳动力。参考铸币厂明特,2017)。众包在这里被理解为众包的一种付费形式,因此被理解为“工作组织的新原则:这里的工作不再通过指令权单独分配;工人们宁愿自己选择工作”(参考文献 Mrass、Leimeister、Fortmann 和 Kolocek穆拉斯和雷迈斯特,2018:139)。通过这种工作形式,20 世纪“标准雇佣关系”兴起后,曾经被认为已成为资本主义过去的工作特征似乎正在回归。参考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2017)。与外包不同,外包是根据固定服务合同将以前在内部执行的任务批量分配给其他公司,而众包则是通过互联网中介平台上的公开征集,向大量未知参与者提供单独且往往是零碎的任务。劳务提供者与劳务使用者之间不存在直接、长期的契约关系,相反,双方以竞争性平台为中介的高度灵活、选择性的关系,被誉为“新的工作模板” '(参考波利尔博利尔,2011:14)。如今德国的众包工作者数量仍然相对较低(参考 Huws、Spencer 和 Syrdal休斯等人,2017;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Pongratz 和 Bormann,2017),但如果众包成为主要的工作模式,而自营职业将越来越多地取代其他更传统的工人,这将对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所有制度体系产生巨大影响和福利国家。即使合同制就业尚未结束,但众包行业似乎已经需要监管。两者均国际化(参考伯格伯格,2016;参考文献 Graham、Hjorth 和 Lehdonvirta格雷厄姆等人,2017;参考 Mandl、Curtarelli、Meil 和 KirovMandl 和 Curtarelli,2017),在德国,对于此类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很多讨论(参考本纳本纳,2014;参考达布罗斯基和沃尔夫Dabrowski 和 Wolf,2017),特别关注劳动法、数据保护、共同决策实践、收入保障和工人保护(参考斯图尔特和斯坦福斯图尔特和斯坦福大学,2017)。
2017 年,德国八个众包平台之一签署了一份行为准则,旨在作为“众包公司和众包工作者之间盈利和公平合作的指南”(Deutscher Crowdaround Verband,2017 年))。至关重要的是,行为准则规定工人应获得公平的报酬。然而,德国的众包工作者认为什么才是正义的呢?他们的期望与传统的、受监管的就业中的员工的期望不同吗?由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并非也在(商业)组织内进行,因此这些期望是否会在他们的绩效无法与传统员工进行比较的领域发生变化?本文探讨了有关众包领域正义感的这些问题。为此,它首先讨论了德国众包和绩效相关正义的研究现状,然后介绍了我们对德语国家使用不同类型众包平台的众包工作者进行的定性和定量调查的结果。
众包:在公司和雇佣合同之外工作
众包工作一般可以定义为:“[……]通过公开招募大量未知参与者,将通常由员工执行的工作外包给组织或个人的策略”(参考帕普斯多夫帕普斯多夫,2009:69)。作为参考 Hertwig 和 PapsdorfHertwig 和 Papsdorf (2017 : 526) 认为,众包与共享经济“仅部分重叠”。在文献中,人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来对各种形式的众包工作进行分类。参考文献 Mrass、Leimeister、Fortmann 和 Kolocek例如, Mrass 和 Leimeister(2018)区分了七种不同的平台类型:上下文/文本创建平台、设计平台、创新平台、市场平台、微任务平台、测试平台和客户服务/市场研究/销售平台(第 17 页)。 142)。除了平台类型之外,其他评论者还引入了额外的分类标准,例如劳动力池、合同类型、算法控制的形式以及建立“数字信任”的来源和机制(参考 Howcroft 和 Bergvall-KårebornHowcroft 和 Bergvall-Kåreborn,2019)。作者基本上根据两个标准区分了四种平台类型:工作是否可靠地获得报酬(即付费工作与非付费工作或投机性工作),以及工作人员(例如专业自由职业者)或客户是否将被被认为是发起者。同时,根据德语国家定性专家访谈进行分类,区分出四种关键平台类型:创新平台、测试平台、微作业平台和设计平台(参考卡瓦莱克卡瓦莱克,2019)。
由于很难对众包工作给出明确的定义,因此很难评估这种做法的普遍程度,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在德国背景下量化这种全球现象。与美国相比,德国众包平台的经济意义仍然较低。2017 年初,32 个众包平台在德国设有总部或至少一个(实体)分支机构(参考文献 Mrass、Leimeister、Fortmann 和 Kolocek穆拉斯和雷迈斯特,2018:142)。在全球范围内,德国“供给和需求都相对较低”(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庞格拉茨和博尔曼,2017:165)。
众包平台本身并没有提供使用其系统的活跃众包工作者数量的可靠数据;他们要么将这些数字视为商业秘密,要么用可能夸大的数字来宣传他们的服务。我们还可以假设许多众包工作者活跃在多个平台上,因此,任何使用这些数字来量化德国或德语国家众包工作者总数的尝试都将具有有限的价值,即使假设更高程度的透明度也是如此。平台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两项研究仍试图对德国或德语国家众包工作者的统计意义做出尽可能容易理解和可靠的估计:
•基于代表性在线调查 (N = 2180),一项比较研究参考 Huws、Spencer 和 Syrdal胡斯等人。(2017 年)估计,145 万(即 2.5%)德国劳动年龄人口至少 50% 的收入来自众包。根据更狭义的定义,该研究还确定了众包工作者的“核心群体”,其中包括那些也使用特殊应用程序来了解工作机会的人。该研究估计,大约有 107 万名“专业”众包工作者生活在德国,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 1.9%
•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Pongratz 和 Bormann (2017)更加谨慎地进行并批评了 Huws 等人。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认为是“误导性的”(第 180 页)。他们估计,过去 10 年里,有 50 万到 100 万人在德国的在线工作平台上建立了个人资料(目前仍然存在)。其中,100,000-300,000 人每月至少从事一份工作,而只有 1000-5000 人从这项工作中获得稳定的收入(与德国平均工资相比(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庞格拉茨和博尔曼,2017:167)。
集体工作无疑对工人有利,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地区。一项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众包工作的长期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指出“不存在简单的剥削故事[……]”(参考文献 Graham、Hjorth 和 Lehdonvirta格雷厄姆等人,2017:153)。尽管如此,研究还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依靠这种工作模式谋生,这种工作模式的风险也会增加。同样,一项针对德国平台运营商的研究(参考文献 Mrass、Leimeister、Fortmann 和 KolocekMrass 和 Leimeister,2018:145-148)表明,众包工作者可以从更大的工作灵活性和额外的收入来源中受益,但必须应对相对较低的工资、缺乏社会保障福利和收入波动。另一方面,众包不仅受益于更大的灵活性和外部专业知识,而且还受益于更大的灵活性和外部专业知识。他们还可以减少开支并节省社会保障缴款。
因此,新形式的数字工作似乎复活了传统劳动力市场机构和谈判过程中明显存在的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安全的“旧”利益冲突。就众包而言,缺乏监管是该行业的系统性而非偶然特征,或者可以这么说:是特征,而不是缺陷。与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平台中介工作不同,纯粹的在线众包工作的特点是工作的“去地域化”和“去个性化”。参考 Menz、Tomazic、Dabrowski 和 Wolf门茨和托马西奇,2017:14-15)。一方面,这对与绩效相关的分配正义产生影响,因为它有助于将全球工资差异与当地生活成本脱钩。另一方面,它影响了与程序绩效相关的正义,因为它导致相关评估标准缺乏透明度以及工人影响这些标准的可能性,同时也消除了(商业)组织提供的社会背景。对于众包工作者来说,这些变化的后果是情感质量(参考 Petriglier、Ashford 和 WrzesniewskiPetriglier 等人,2018)。
工作场所的表现和不公平感
参考杜贝特Dubet (2008) 的定性研究重新激发了学术界对工人对工作场所不公正的看法的兴趣,他将其概念化为“规范活动”,具有“被认为合法的原则的整体”和“自治”的双重意义。独立判断的决定'(参考杜贝特杜贝特,2008:17)。根据 350 次采访,杜贝特认为,工人对不公正看法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平等、绩效和自主。对于众包工作者来说,平等和自治的原则不太重要,因为众包工作者不可能将自己与其他工作者进行比较,并且根据定义是完全自主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关注性能。与绩效相关的正义意味着一个人因所做的工作而获得公正的报酬(参考杜贝特杜贝特,2008:24)。对于杜贝来说,表演的概念既包括“行动的客观结果”,也包括“行动者的参与”。因此,“绩效的矛盾心理”不断地“在客观有用性和付出的努力之间摇摆”(参考杜贝特杜贝特,2008:127)。在 Dubet 的基础上,过去几年针对德国员工的正义期望进行了两项大型定性研究。
•参考 Hürtgen 和 VoswinkelHürtgen 和 Voswinkel(2014)对由“普通”员工组成的群体进行了 42 次传记访谈,即具有长期雇佣合同和中级资格的中年工人(参考 Hürtgen 和 Voswinkel许特根和沃斯温克尔,2014:39-40)。在访谈中,工人们表达了“具有普遍规范力量的价值观”,其基础是他们作为人类和具有生产能力的社会人的基本观念。从他们的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他们与收入相关的期望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获得适当的报酬来表达的(参考 Hürtgen 和 Voswinkel许特根和沃斯温克尔,2014:139-140)。从他们的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看,良好的收入被视为“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规划保障以及他们应得的社会保障福利和养老金提供的期望。参考 Hürtgen 和 Voswinkel许特根和沃斯温克尔,2014:145-150)。一般来说,收入既被视为“对[……]成就的奖励”,又被视为“对一个人生产能力的象征性认可”(参考 Hürtgen 和 Voswinkel许特根和沃斯温克尔,2014:149)。
•另一项社会学研究(参考 Kratzer、Menz 和 Tullius克拉泽等人,2015;相似地参考图留斯和沃尔夫Tullius 和 Wolf,2016)根据对德国非管理员工的 320 次定性访谈,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工作合法化。除了期望在工作场所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参与直接工作环境中的决策以及维护尊严的工作条件外,受访者还表达了对与绩效相关的正义作为以努力为中心的概念的主观期望。作者将员工的规范性期望解释为对合法性的要求,这些规范性期望“在特定的组织规则(例如分配规则、决策程序和危机管理措施)的背景下明确或隐含地制定”。参考 Kratzer、Menz 和 TulliusKratzer 等人,2015:14)。在技术工人中,与绩效相关的公正性衡量标准与工作场所的努力概念相关,而在“知识工人”中,与绩效相关的公正性衡量标准与努力做好准备相关(Kratzer et al., 2015: 50-51)。
除了这些阐明对工作的各种期望的复杂性的定性研究之外,还有一项定量研究(参考施耐德Schneider,2018)根据德国社会经济小组(SOEP)的数据表明,德国大多数传统雇员认为他们的薪酬是公平的。大约 61% 的工人(64% 包括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总收入公平,但只有 55%(56% 包括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净利润公平。在几乎所有群体中,总收入被认为比净利润更公平。有趣的是,只有 59% 的全职员工认为自己的总收入公平,而兼职员工和临时工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62% 和 79%(Schneider,2018:366)。
即使在那些从事“迷你工作”的人中,比如众包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额外的收入来源,但通常工资较低,提供很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保护,并且涉及零时合同,77%的员工认为良好的收入很重要或非常重要,而 82% 的人认为与其绩效相匹配的收入同样重要或非常重要(参考贝克曼贝克曼,2019:251-342)。在这两个方面,2016 年员工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匹配度很差:良好收入的匹配度仅为 47%,与绩效相关的公平收入的匹配度为 48%(参考贝克曼贝克曼,2019:293)。
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导向绝不限于众包领域;在更传统的雇佣关系中,近年来,与绩效相关的政策越来越多地从以努力为导向的方式转向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参考布赖西格布赖西格,2018)。正如 Menz 和 Niess(2017)指出的那样,员工并不认为管理方法从努力到结果的转变“根本上是非法的”,但它也不构成“独立的正义原则”(第 133 页;见脚注 12)。然而,众包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上述研究中考虑的工作类型(包括“迷你工作”)相比,众包工作并不发生在(商业)组织内。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这一原则的形成问题”(参考文献 Menz、Nies、Behrmann、Eckert 和 GefkenMenz 和 Nies,2018:132-133)得到了解决,并且由于屡屡侵权,对与绩效相关的正义的需求仍然是“冲突和批评的持久根源”(参考图留斯和沃尔夫图留斯和沃尔夫,2016:496-497)。由于众包工作缺乏这种组织背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批评空间),因此我们不知道众包工作者对与其工作绩效相关的不公正的看法会发生什么。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从实证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提出对与绩效相关的正义看法的定性研究的结果。我们使用这项研究的结果来生成用于定量研究的调查工具的项目,该定量研究将在后续部分中描述,以了解众包工作者对绩效相关正义的态度。
了解正义和众包:方法论
先前关于传统雇员和商业组织中与绩效相关的公平性的研究结果是否也可以应用于众包工作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并从参与者的不同角度获取与绩效相关的正义方面的信息,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实证调查。本节详细介绍的第一阶段是定性和探索性的。
定性样本和数据
该研究(参见参考卡瓦莱克Kawalec,2019)包含了对从事众包工作或了解众包工作的人员的 18 次采访。由于目前缺乏关于众包的哪些方面是典型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案例选择的目标是捕获具有不同众包经验的个体样本,以便产生定量调查的问题。为此,我们对一家正在将部分业务转向众包的大公司的员工进行了 11 次半结构化定性访谈。此外,还采访了 18 名众包工作者。其中三名众工活跃在测试平台,七名活跃在创新平台,三名活跃在设计平台,五名活跃在微作业平台。此外,还有七位专家访谈(参考格拉泽和劳德尔Gläser 和 Laudel,2010)由学术和政治专家以及平台运营商进行。抽样和分析是在扎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参考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格拉泽和施特劳斯,2009)。访谈是半结构化的,允许开放式的回答。由于来自其他案例的新信息量接近于零,因此停止纳入新的受访者。使用 MAXQDA 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录和编码,目的是识别受访者经常提到的概念和概念类别。使用数字社交网络结合滚雪球抽样来选择潜在的访谈伙伴,要求访谈伙伴识别其他潜在的研究参与者(参考 Przyborski 和 Wohlrab-SahrPrzyborski 和 Wohlrab-Sahr,2010)。数据收集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进行。所有参与者都居住在德语国家。
定量在线调查:项目和研究设计
定性研究表明,规划安全、绩效评估、任务描述和薪酬等主题是众包工作者对工作公平性的体验和期望的核心。我们在定量调查项目的开发中采用了这些主题,如下所述。
我们从最近的两项研究中提取了一些内容,这些研究涉及众包领域绩效相关正义的收入特定维度(参考 Alpar 和 Osterbrink阿尔帕和奥斯特布林克,2018;参考叶、你和罗伯特叶等人,2017)。这些研究不仅询问了众包工作者的“薪酬公平感”(PFP),还询问了众包工作者的“薪酬公平感”(PFP)。他们还将这个问题与 MTurk 等微任务平台上专门设计的测试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观察到 PFP 与绩效质量之间的联系(参考叶、你和罗伯特叶等人,2017:333)。
作者在 PFP 上为众包制定了三项:(1)“我的付款反映了我在任务中投入的努力”,(2)“我的付款适合我已完成的工作”,以及(3)“我的付款”考虑到我的表现,这是合理的”(第 330 页)。这些项目又改编自参考科尔奎特Colquitt (2001) 的组织正义量表 (GEO),适用于德国环境并由参考文献 Maier、Streicher 和 Jonas迈尔等人。(2007)。
GEO由四个量表组成,分别涉及程序正义(7个项目)、分配正义(4个项目)、人际正义(4个项目)和信息正义(5个项目),李克特型量表从1(不包括全部或几乎从不)到 5(完全或经常;Maier 等人,2007:101)。作者强调,向受访者解释调查的方式和一些项目表述可以改变以适应新的研究问题(Maier 等,2007)。为了纳入上述定性结果,我们采用如下 GEO 的各个维度来收集数据(附录中的表 1A ) 显示项目的配方以及它们与参考文献 Maier、Streicher 和 Jonas迈尔等人。(2007)。我们的改变是出于以下考虑:
•由于众包不涉及与上级的任何接触,因此人际正义的维度不适用
•程序正义涉及决策过程(在我们的例子中,涉及制定和评估任务的过程)以及决策过程被视为能够受到影响的程度。三个程序项为评估绩效评估维度的四个项目提供了基础,另一个程序项启发了任务描述维度的项目的制定
•在参考文献 Maier、Streicher 和 Jonas迈尔等人。(2007),信息正义是指决策者的信息特定行为(例如,这些人是否诚实或及时提供信息)。然而,在我们的上下文中,它指的是平台介导的流程。使用两个项目来评估绩效评估和任务描述的维度。
•分配正义主要关注个人贡献(其工作的质量和数量)与从中获得的收入之间关系的公平性。两个分配性GEO项目激发了薪酬维度上的两个项目。
为了招募研究参与者,我们在三个德语在线平台上联系了众包人员,以进行测试、创新和设计或微型工作。我们使用平台本身来寻找参与者,并使用 Unipark(现为 Questback)进行调查。
调查样本:描述性特征
共有 230 名众包工作者参与了调查(测试、创新和设计 N = 121,杂项微工作 N = 99)。女性(47.4%)和男性(52.6%)的参与者人数几乎相等。平均年龄为 39.1 岁(N = 227;SD = 12.6),最年轻的参与者报告年龄 19 岁,最大的 73 岁。大多数参与者 (62.5%) 表示他们已完成学术学位(26.6% 拥有拥有应用科技大学学位(35.8% 拥有大学学位),而 37.6% 则拥有职业职业。同样,超过 47.2% 的人表示他们是全职工作,16.6% 是兼职工作。总体而言,17.9% 的人称自己处于失业状态,另有 18.3% 的人从事迷你工作或目前正在接受培训。参与者平均在 1.7 个平台上工作(N = 224;SD = 0.909),最多的是5个平台,但54.9%的大部分集中在1个平台。据报道,每月平台上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48.4 小时(N = 215;SD = 58.341,每月最多 392 小时)。我们的样本中 94.4% 的人不是在路上或在正常工作中执行平台任务,而是在家中进行众包工作。
平均而言,受访者每月在平台上工作 40 小时 (N = 216),其中 8.8% 的人每月工作 100 小时或以上,其中一位受访者报告最高工作时间为 392 小时。我们的样本与其他众包研究的样本没有显着差异。参考 Huws、Spencer 和 Syrdal胡斯等人。(2017)根据样本估计,德国 61% 的众包工作者为男性,39% 为女性,52% 的人群年龄在 16 至 35% 之间,63% 从事全职工作。根据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Pongratz 和 Bormann (2017)也是如此,大多数众包工作者受过大学教育,年龄在 30 岁以下。根据引用的研究,该行业男性工人的比例在 50% 至 68% 之间(第 168 页)。 脚注1
定性调查结果:理解正义期望
根据众包工作者的采访,我们绘制了众包的四个领域,其中阐明了与绩效相关的正义的期望。其中一个中心区域正在规划安全。众包工人永远无法确定他们将获得多少工作以及最终是否会获得报酬,而这种缺乏安全感的问题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只有当众包工作作为一种额外的收入来源而不是其他收入来源时,这个问题才会得到缓解。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下是对此问题的两种典型回应:
缺点是你不能真正指望固定工资。我的意思是,我不能说:在月底我总是会得到我的固定工资,无论多少欧元——你只是不能依赖它。(“巴斯蒂安·布赫曼”,测试平台,11:101) 脚注2
你在做某事。你投入时间[…]。然后发现它没有被使用,那么你的工作就白费了。[…] – 是的,你工作,而且通常你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但你却一无所获。然后它就不起作用了。然后整个纸牌屋就会倒塌。(“诺曼·诺伊兰”,设计平台,17:18)
规划安全问题与绩效评估的公平性密切相关。对此,受访者抱怨评价标准缺乏透明度,他们没有可能对这些或评价过程本身施加影响或提出反对意见。尝试提出此类反对意见可能会遇到非常简单的障碍,如下例所示:
你不认识他们。你也不能和他们争论。您可以通过支持让他们知道[...]但是对于您得到的这些少量资金,真的吗?因此,对于这一欧元付款,我是否应该向他们发送另一封电子邮件[…?]。然后我对自己说,‘啊,不,我会继续下一份工作’。(“梅丽莎·穆勒”,设计平台,22:45)
另一个问题领域是评估历史,这可能导致评估过程中不公正的积累:
只是,当你被拒绝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时,你可能无法获得某些工作。那里只是说:只有当您在该类别或来自该客户的分数达到 90% 时,您才能继续。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么在几周、几个月内,无论多久,你都会被封锁,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Klaus Klein”,微任务平台,21:80)
然而,众包工作者不仅会因为自己的评价而感受到不公正感。他们还因为任务描述不够清晰而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格尔达·格拉斯 (Gerda Grass) 指出,这些任务通常“有点太不具体”或“犹豫不决”(设计平台,16:64)。由于任务描述最终会影响众包工作者是否获得报酬,因此模棱两可或矛盾的描述不仅会让众包工作者感到沮丧,而且还会影响众包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它们还影响他们更广泛的公平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写信给他们,‘如果你们要向我们提供简报,那么他们必须说清楚。那个时候是关于例句的。[…] 上面说:“你需要至少给出两个例句”,但下面又说:“一个例句是强制性的。” 两个就好了’。(“Martin Mönch”,微任务平台,24:46)
无论哪个平台,受访者都认为薪酬水平不足。有些人将他们的潜在收入与其他形式的第二职业进行比较,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赚了两、三欧元”。这不值得。你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你最好还是去修剪草坪”(“Pawel Polanski”,微任务平台,14:22)。其他人将低潜在收入与客户和平台运营商的利润进行比较,例如“整个事情是一项数百万欧元的业务 [...] 这是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Fritz Freudig”,创新平台,15:45 )。许多受访者还抱怨工作的报酬与所需的努力不匹配,就像下面的例子:“你做很多事情却报酬很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报酬。” 所以这是一种剥削形式”(“Sigmund Schlecht”,创意平台,19:41)。请注意,接受采访的众包工作者并不认为缺乏社会保险福利有什么问题,这一发现似乎令人费解。然而,受访者在德语国家工作,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都很低,社会福利也很高,与就业状况无关。因此,这些众包工作者并不依赖他们的众包工作来获得健康保险或退休福利。
定量研究结果:衡量正义期望
在提出定量研究结果之前,了解我们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非常重要。我们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收集了 28 个态度项目的数据((-2) = 非常不同意;(-1) = 不同意;0 = 尚未决定;1 = 同意;2 = 强烈同意)。大多数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大多数项目,这种有限的变化使得响应模式的识别不可靠。此外,由于问题不是随机的,任何协方差的解释可能会受到连续的人工制品和改变的项目公式的阻碍。然而,由于各种方法论原因,可以排除问题、组和条件之间的结论性比较。此外,例如,利用现有数据不可能以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形式对维度进行定量验证。为了与这项研究的探索性特征保持一致,我们现在将粗略地介绍一下描述性数字:
附录中的表 1A详细列出了规划安全、绩效评估、任务简报和等维度的结果。图 1 比较了工人对众包工作的期望(fair_c_*;浅色/灰色)和他们对常规就业的期望(fair_w_*;深色/灰色)。我们的定性结果已经表明,员工缺乏计划众包领域的安全是不公正的一个具体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众包工作只是第二职业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受访者对众包工作和投标稳定流动的期望(“公平_*_1”)仅略低于传统就业(图 1,顶部第一条)。
由于众包平台的结构性匿名性和缺乏透明度,缺乏影响或反对绩效评估及其标准的机会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定性访谈中提出的。“公平_*_2”至“公平_*_6”项目的定量数据强调了该问题的相关性,尽管影响绩效评估的可能性似乎被认为不如绩效相关正义的其他方面重要(图 1,如下)酒吧)。
与定性数据一样,定量数据表明,不明确或矛盾的任务简报常常构成感知不公正的进一步根源。项目“fair_*_7”和“fair_*_8”被认为很重要,甚至可能比常规就业更重要(图 1)。定量结果还证实了有关“fair_*_9”和“fair_*_10”项目薪酬重要性的定性结果。尽管如此,受访者认为众包工作 (_c_) 中的公平薪酬与传统就业 (_w_) 中的工作同样重要(图 1,最后几条):
总结感知正义所有 10 个维度的指数(表 1)还揭示了对众包工作的期望(N = 188,平均值 = 1.04,SD = 0.673)和有酬就业(N = 180,平均值 = 1.06,SD = 0.550)。按当前就业状况比较指数值时,几乎观察不到任何变化。中位数和平均值略有不同,差异在分布中更为明显。目前未就业的受访者对正常就业的期望最高(图 2 ,蓝色箱线图)。然而,所有差异通常都很小,而且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经验似乎对报告的期望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性别或众包中的每月工作量(使用群体中位数作为截止值,可操作为平均或低于平均水平与高于平均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表 1和图 3):
总之,我们的定量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了定性访谈的结果。众包工作者的正义期望在众包工作和传统就业之间差别不大。但请注意,该调查仅是探索性的,并未声称代表所调查平台上的众包工作者或一般众包工作者。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群的社会人口统计数据,因此无法分析研究样本的差异。
结论和启示
我们的结果证实了现有关于员工对绩效相关公平的期望的研究,并表明众包工作者的公平期望与传统工作安排中员工的公平期望相似。然而,我们不知道(并且我们的数据不允许我们对此得出任何结论)这种共性是否是由于某种形式的转移(因为大多数受访者通过传统的就业形式谋生,并有可能继承他们的的期望),和/或这种相似性是否是一种过渡现象,如果传统雇员越来越多地被个体经营者取代,这种现象在未来可能会加剧。
尽管如此,我们观察到,众包工作者确实阐明了与绩效相关的正义原则,并且他们根据平台中介工作的负面经历制定了这些原则。因此,尽管德语国家的众包工人自愿从事低薪工作,并同意与传统雇员相比,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受到较差保护的雇佣关系,但他们仍然认为众包和传统就业形式具有相似的正义标准。
我们的研究对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影响。迄今为止,关于众包工作者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安排的研究还很少,但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众包工作者确实认为他们的工作安排不公平,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四个具体问题领域:规划不安全、缺乏透明度。在绩效考核中,任务说明不明确、薪酬偏低。如果未来旨在支持众包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针对这些特定领域,可能会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斯图尔特和斯坦福斯图尔特和斯坦福(2017)提出了监管平台中介工作的广泛制度选择。作者指出,可以明确或扩展“就业”和“雇主”的定义,以创建一个可以应用现有监管标准的新的“独立工作”监管类别。这将使得不仅可以向传统安排中的雇员,而且还可以向零工经济中的个体经营者授予工人权利(目前所接受的)。我们的发现是,众包工作者在众包工作中对正义的主张与他们对传统就业的主张相似,这表明,将现有的监管标准应用于众包工作,正如斯图尔特和斯坦福所概述的那样,至少从众包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
尽管我们的定性和定量结果得到了强有力的交叉证实,但这些数据在做出一般推论方面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主要面向传统就业形式,因此缺乏可比数据。有关此困难和各种可能的数据收集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另请参阅参考 Pongratz 和 Bormann庞格拉茨和博尔曼(2017:179-181)。此外,与所有关于众包的研究一样,我们的调查面临着众包平台不公开其数据的困难,这阻碍了对当前活跃众包的总数和人口统计数据的评估。
谈谈我们关于正义和就业的规范立场。在评论中参考杜贝特Dubet (2008)对工作场所不公正看法的研究,参考文献 Kronauer、Misselhorn 和 BehrendtKronauer(2017)指出,排斥和不公正是传统就业的必要特征,因此暗示员工可能或多或少经历正义的想法是虚构的。为了参考文献 Kronauer、Misselhorn 和 BehrendtKronauer (2017) 认为,真正的不公正之处在于,虽然一个人是否被纳入有酬就业模式据说与自己的绩效挂钩,因此是根据与绩效相关的正义标准来判断的,但工人实际上与他们所关注的总体市场机制挂钩。无力影响(第 237 页)。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的方法是从表面上理解工人对工作安排中的正义和不公正的看法。如果工人能够阐明正义标准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工作安排中,那么我们相信他们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具有有效性,并且对社会政策具有意义,而与他们改变世界的能力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