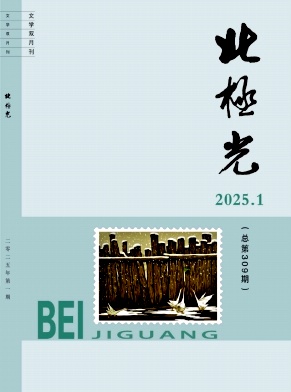新闻资讯
介绍
本文的目的是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经济、规范和技术趋势的背景下评估 30 年的气候谈判。第一部分将回顾气候谈判的历史,然后分析第 26届和第 27届气候谈判的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缔约方大会于 2021 年 11 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COP26),并于 2022 年 11 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 (COP27)。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评估气候话语的演变,并考虑随时间推移的政策和技术趋势。第三部分将简要评估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减排努力中发挥的相对作用。主要论点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鼎盛时期已经结束。势头已从国际谈判转向国家和次国家行为者,并越来越多地从政府转向社会和私营部门行为者。
国际关系学者大多认为气候危机是一个集体行动/搭便车问题,它将富裕国家的历史责任与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贡献相对立,其中美国和中国是关键参与者(Stern ,2007;Aldy & Stavins, 2009;维克多,2001)。气候谈判被视为零和游戏,其中唯一重要的是各国之间减排成本的分配。这种想法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气候谈判变得更加激烈,而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似乎越来越不可能。然而,实证主义的结构分析掩盖了美国在阻碍有效的气候制度方面所发挥的霸权作用(深深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Oreskes ,2010;Clémençon, 2008,2010 ;Skocpol,2013)。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际谈判对各国实际在国内所做的事情有很大影响(Aklin & Mildenberger,2020)。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与国际气候谈判动态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气候政策相关事件。需要更多关注来了解道德框架如何激励国内政策以及它们如何与国际层面发生的事情相互作用(Cashore & Bernstein,2022))。随着各国面临气候危机带来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人们对成本效益的考虑也发生了变化,代际因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的国内能源和气候政策决策越来越受到经济和道德气候正义考虑因素的影响,这些考虑因素认识到代际权衡以及主要污染者和遭受后果的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Timmons&Parks,2009年;Sinden, 2010;Newell 等人,2021)。一些研究还表明,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可能比政策制定者假设的要大(Poushter 等,2022;Sparkman 等,2022)。
本介绍的以下部分首先回顾了气候危机的状况,然后简要描述了可能使 2022 年成为对抗温室气体排放的转折点的因素。
正在发生的气候危机
2022 年,全球变暖继续其无情的轨迹。最近的八年,即 2015 年至 2022 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八年。世界气象组织预计 2021 年全球平均气温比 1850-1900 年平均气温高 1.11 ± 0.13°C(WMO,2022)。然而,全球平均水平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
2022 年,极端天气事件继续造成创纪录的破坏。热浪袭击了西欧、北美和亚洲,加剧了西班牙和法国的灾难性野火,并在许多国家创下了新的全国气温记录。北极和南极洲的极端气温远高于正常水平,冰层流失加速。2022 年 8 月下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首先遭遇另一场创纪录的热浪,随后又遭遇暴雨。季风暴雨淹没了巴基斯坦 1/3 的地区,造成 1100 多人丧生,数百万人失去家园。十月,佛罗里达州的伊恩飓风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洪水。2023 年伊始,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毁灭性洪水,欧洲 1 月份气温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联合国报告发现,“没有可靠的途径”将气温升高控制在 1.5°C 以下,这是科学家们认为人类不应突破的阈值,也是《巴黎协定》中商定的目标(UNEP,2022b)。目前的政策意味着气温将上升 2.8°C 左右。唯一的积极消息是,在 2015 年巴黎会议之前,世界进一步偏离了轨道,当时预计未来气温升高高达 3.5°C(UNFCCC,2021b)。2022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417 ppm,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51%,同时化石燃料和水泥产生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 36.6 吉吨二氧化碳 (GtCO2) 的新纪录(Friedlingstein 等,2022))。
2022年会是一个转折点吗?
在气候危机不断蔓延的背景下,国际气候谈判对于任何关心地球未来的人来说都是极其令人沮丧的。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后续进程陷入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强权政治之中,涉及历史性贡献、持续依赖化石燃料扩张以及未能履行财政承诺的责任分配。青年运动的新偶像 Greta Thunberg 将 COP26 称为“blahblahblah”俱乐部,并跳过了“绿色清洗”COP27(Dickie,2022)。从表面上看,这种评价很难反驳。
2021 年和 2022 年的最后两次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召开的,其任务是审查实现巴黎目标和加强国家承诺的成功情况。他们远远没有采取更强有力的承诺来应对从现在到 2030 年之间的关键时期,以保持 1.5°C 的升温上限成为可能。2022 年 11 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通过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为气候正义倡导者取得了历史性(尽管目前只是象征性的)胜利。
国际气候谈判必须放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全球趋势以及国家政治转折点的背景下看待。在俄罗斯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入侵乌克兰之前,多边主义就已经面临严峻挑战(Nye,2017;Kornprobst & Paul,2021;Low,2022)。世界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贸易冲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自由民主国家的衰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威权主义的强化。对多边解决方案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使得单边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唯一的希望。主要国家的一些不相关的政治事件和选举结果表明,转折点可能即将到来。
主要国家最近的几次选举带来了重大的政治转变。在美国,民主党人乔·拜登于2020年11月3日当选总统。202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提供3700亿美元的气候相关融资,主要是税收抵免和补贴(Paris et al., 2022) 。继 1992 年和 2009 年通过能源和气候法案的类似努力失败后,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本身就使美国走上了在未来十年实现大幅减排的轨道,即使这只是实现所需目标的一个开始。
在德国,在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力帮助下,由社会民主党奥洛夫·肖尔茨担任新总理的中左翼联合政府于 2021 年上台。新联合政府结束了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下长达16年的中右翼政府。尽管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默克尔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在气候政策上过于缓慢和胆怯(Töller, A., 2022)。德国新政府立即着手推行更加雄心勃勃的气候和能源政策,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家能源安全危机之前。绿党现在拥有重要的气候政策相关部委。欧盟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经济和气候部被合并为绿党领导人罗伯特·哈贝克领导的一个超级部。他的党内同事安娜莱娜·贝尔博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作为乌克兰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以及大幅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而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2022年11月举行的最新气候会议上,她带领德国和欧盟呼吁在2030年之前做出强有力的减排承诺。Bauchmüller 和 Braun,2022)。
近年来遭受一系列极端干旱和洪水事件的澳大利亚,在 2022 年 5 月大选后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工党成功推翻了保守派斯科特·莫里森,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承诺澳大利亚将到 2030 年,排放量比 2005 年水平减少 43%,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Cleary & Fumei,2022)。气候变化是导致年轻人投票反对莫里森的一个重要因素。
2022 年 10 月,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 (Lula Da Silva) 击败极右翼气候否认者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赢得大选,在博尔索纳罗的领导下,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近年来达到了新的高度。达席尔瓦承诺扭转亚马逊破坏性的开发,并与印度尼西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一起加入热带国家俱乐部,承诺停止砍伐森林并永久保护其大片森林(路透社,2022 年)。
也许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涉及贸易规则在支持各国零排放进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国际供应链的普遍重新思考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即使单边贸易措施没有合法化,也已经正常化。有充分的理由对修补已经脆弱的贸易体系保持谨慎(Jackson,2008;Low,2022)。但国际竞争压力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碳税和其他环境产品标准的强大抑制因素,而且早就应该在贸易规则中认真考虑气候目标(Clémençon,1995); 查诺维茨,2020;莱昂内利,2022)。
近几个月来,美国和欧洲提出或出台了旨在加速绿色能源转型的补贴、关税和其他政策(Banker,2023;Swanson,2023)。然而,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包含的与气候相关的税收抵免和补贴与贸易规则背道而驰,因为它们只支持国内电动汽车生产商。2022 年 12 月,欧盟对不符合欧盟公司必须遵守的气候保护标准的外国公司进口商品征收前所未有的碳税(美联社,2022 年))。该税预计将于2023年10月生效,并于2027年全面实施。只有与欧盟具有相同气候目标的国家才能够向欧盟出口而不受该税的影响。新规则旨在确保欧盟的气候努力不会因生产从欧盟转移到政策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受到损害。
此外,气候诉讼已成为追究污染者责任的主要因素。法院越来越支持气候正义倡导者,他们声称气候危机的主要责任者正在危及当前和未来的人权(Abate,2016;Ekardt,2022)。它们迫使政策和投资决策发生真正的变化,并已经阻止了一系列新的化石燃料项目在世界各地的推进(Mishra,2022)。在 2021 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荷兰法院命令壳牌到 2030 年将碳排放量减少 45%。一些高风险的气候诉讼案件将于 2023 年做出裁决(Kaminski,2023)。
一项罕见的多边成功是在 2022 年 12 月通过了一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历史性协议。该协议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内谈判达成的,要求保护 30% 的地球并恢复 30% 的退化土地,以换取到 2030 年,为保护提供 300 亿美元的资金(IISD,2022a;Greenfield,2022)。该协议定义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作用,并强调了气候危机与对既充当碳汇又充当气候调节器的关键生态系统的全球保护之间的协同关系(Dinerstein等人,2019)。
最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看法,并增强了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战略,特别是在欧洲,因为总体上更加独立于外国化石燃料的需要变得越来越明显。此后,所有欧洲政府都通过了法案,大大加速了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欧盟委员会也紧随其后,提出了一项新的绿色协议工业计划提案,以重建欧洲工业实力(欧盟,2023年;经济学家,2023年)。
最近的这些政治事件本身并不会改变 2023 年全球变暖轨迹。随着政治潮流的变化,其中大多数都是可逆转的。然而,总的来说,他们表明政治势头正在转向比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果断的国家气候政策,其中两个最富有的经济体——欧盟和美国——以不同的方式引领潮流。
多年来的气候谈判
下文将追溯从 1992 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1997 年《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到 2015 年《巴黎协定》的达成协议,国际气候制度的演变。本节最后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两次年会(2021 年 COP26 和 2022 年 COP27)辩论的头条问题。这些是从现在到 2030 年期间的承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补贴,就“损失和损害”资金达成协议机制,以及如何实现长期气候融资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必须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巴黎气候协定》。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通过之前,主要由欧洲小国领导的欧盟一直在推动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 (GHG) 减排目标和时间表,但美国拒绝了此类目标(Chatterjee & Finger,1994;Leggett,2001;Clémençon,2010)。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才放弃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反对,经过艰苦的谈判,《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获得通过。《京都议定书》确实承诺发达国家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 2008 年至 2012 年的承诺期内,比 1990 年的水平至少减少 5%。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了 8%、美国 7% 和东道国日本 6% 的减排目标。
发展中国家无需接受基于《1992 年里约宣言》(原则 8)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4 条)中商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的具体排放目标。CBDR原则规定,发达国家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将首先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国家减排措施,然后发展中国家才能效仿(Agarwal & Narain,1991;Dubash,2009)。1987 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这种方法开创了先例。它坚定地建立在逐步淘汰目标和时间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区分的基础上(Benedick,1991; 韦特斯塔特,200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在 1987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逐步淘汰臭氧消耗物质的谈判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欧洲大型经济体则落在了后面。
在欧洲国家同意让各国利用“灵活机制”实现减排(即“共同减排”)之后,美国才接受了《京都议定书》及其目标和时间表。灵活性机制包括一系列碳抵消,从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到国家之间的排放权交易。它削弱了各国应首先从国内源头减少排放的最初想法。
然而,2001年,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且微弱的选举胜利之一的总统后,美国退出了该协议。尽管《京都议定书》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批准并于 2005 年生效,但之前的主要支持者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后来也跟随美国的脚步退出了(Clémençon,2008 年;2010 年)。然而,欧盟继续履行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并建立了欧盟范围内的强制性排放交易机制(Skjærseth 和 Wettestad,2008 年))。关于《京都议定书》让中国和印度摆脱困境、让美国合法化退出该议定书的做法,已经有很多文章阐述了这一点。但真正的原因是化石燃料行业对国会的影响(Pope & Rauber, 2004 ; Oreskes, 2010 ; Pooley, 2010 ; Supran & Oreskes, 2021)。美国未能兑现采取第一步限制排放的最初承诺,至今仍继续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许多政府对气候谈判的干预充分证明了这一点(Dubash ,2019;IISD, 2021,2022b )。
巴黎协定:从目标和时间表到国家自主贡献(NDC)
《京都议定书》涵盖的时期一直到 2012 年。欧盟就 2012-2020 年期间第二个《京都议定书》进行谈判的尝试最终在 2009 年的哥本哈根 COP16 上停止(Clémençon,2010)。新当选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k Obama)不想在新一轮能源和气候法案的推动刚刚失败后与美国国会作对( Pooley, 2010 )。相反,美国试图说服欧盟放弃对目标和时间表的坚持,支持开放、灵活的协议架构,其中包括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
《巴黎协定》反映了对美国政治机会结构的现实评估,尽管存在重大缺陷,但仍标志着前进的道路(Clémençon,2016;Dimitrov 等,2019)。它通过接受科学共识来定义一个关键的全球规范标志,即世界必须将工业化前时期的升温控制在 1.5°C 以下,以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危机。小岛屿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游说可以归功于之前 2°C 限制的下调。
巴黎协议只有在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不包含要求各国采取国内法律行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该协议呼吁各国提交并定期更新国家自主贡献预期(INDC),现在通常称为 NDC。它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周期,各国通过该周期规划和传达其国家自主贡献,然后实施其计划,并审查个人和集体的进展,为未来的规划和下一个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巴黎谈判最终放弃了将公平和环境正义考虑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方法的明确基础。作为回报,它提供了一项普遍协议,该协议首先为美国所接受,而且对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也具有规范约束力。但如何在巴黎后续行动中建立公平性仍然是一个中心问题(卡尼特卡,2019;温克勒,2019)。
2021 年和 2022 年《巴黎评论》:渐进主义以保持 1.5°C 的活力
新冠疫情导致国家自主贡献(NDC)五年期审查推迟至2021年,届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最终在格拉斯哥召开。会议的任务之一是完成实施和报告国家自主贡献的技术指南(通常称为“巴黎规则手册”)(IISD,2021;例如,WRI,2022))。COP27 于 2022 年 11 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讨论承诺的充分性并制定实现更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方法。会议继续在技术和程序问题上采取渐进的步骤,但未能就如何加速全球减排以符合《巴黎协定》保持在 1.5°C 以下的目标达成任何政治突破。
保持在 1.5°C 以下和 2030 年目标
2022 年 9 月提交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 (NDC) 计划将导致到 2100 年气温升高 2.6°C(如果全面实施),而现行政策将导致气温升高 2.8°C,这突显了国家承诺与履行这些承诺的努力之间的差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22)。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不依赖于财政支持,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交的有条件国家自主贡献列出了以发达国家提供充足气候融资为条件的措施。它们仍会导致气温升高约 2.4°C。这些估计强调了将气温控制在 1.5°C 以下的挑战以及必须大幅削减排放量。承诺的雄心问题一直是谈判和新闻报道的焦点,但国家自主贡献的透明度、一致性和可实施性最终是关键要素(Pauw&Klein,2020)。
2021 年 COP26 所采用的措辞勉强维持了防止世界升温超过 1.5°C 的可能性。经过多次争议,通过的文本承认“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 需要快速、深入和持续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 2010 年水平减少 45%,并实现净零排放”。大约本世纪中叶,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大幅减少(UNFCCC,2021a)”。与几天前分发的呼吁“到 2100 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的文本草案相比,此次采用的措辞是一个重大改进。这将允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只要到本世纪末将温度降低到 1.5°C(可能是通过从大气中去除碳),温度升高就会超过 1.5°C。
2022 年 11 月的埃及会议勉强确认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C 的目标。让许多国家和环保组织感到非常失望的是,缺乏有力而具体的语言来加大力度在 2030 年之前减少排放,而研究表明,“保持 1.5°C 的目标”正在逐渐消失。在会议期间的某个时刻,一份文本草案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一提及。欧盟和许多最脆弱的国家将此归咎于石油生产国,并威胁说,如果格拉斯哥采用的语言出现倒退,这些国家将退出(Kottasová,2022)。
尽管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粮食生产排放首次在缔约方大会上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牲畜排放量几乎占全球人为排放的甲烷排放量的 1/3,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Stoll-Kleemann & O'Riordan,2015)。但非政府组织通过采取“肉类峰值”决定来关注人类饮食、摆脱肉类和奶制品养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相反,COP27 的重点是奶牛的饮食,以减少它们打嗝时产生的气体。环境组织警告说,随着参加埃及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代表人数急剧增加,工业农场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Lakhani,2022)。“气候智能”食品生产已成为新的流行词,该行业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净零乳制品、精准农业和滴灌技术等高科技解决方案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批评者认为这些努力主要是对现有有害农场做法的重新命名。
工业食品生产因其巨大的土地使用足迹、巨额政府补贴以及与化石燃料行业的密切联系,已成为气候活动人士的新战线。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成功的。
直接针对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继续提供全球一次能源的 80% 以上,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快速增长(IEA,2021)。化石燃料和水泥产生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 2022 年创下 366 亿吨二氧化碳 (GtCO2) 的新纪录(Friedlingstein 等,2022)。放弃煤炭这种最肮脏的化石燃料对于将气温升高控制在 1.5°C 以下至关重要。环保组织和许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减少化石燃料补贴,作为长期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第一步。但全球 51 个国家的政府对化石燃料的支持几乎翻了一番,从 2020 年的 3,620 亿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6,970 亿美元(IEA,2022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能源价格上涨,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各国(尤其是贫困国家)面临着减少补贴的压力,这些补贴导致能源价格走低。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到 2030 年,全球现有 8,500 座燃煤电厂中的 40% 必须关闭,并且不能建造新电厂,以保持在 1.5°C 的限制之内(IEA,2021 年)。2021 年 COP26 的一场主要政治斗争是关于逐步取消煤炭补贴。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反对,一项呼吁“逐步取消不减量的煤炭和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提案在大会全体会议的最后一个小时被改为“逐步减少”。
明确呼吁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逐步淘汰煤炭并不令人意外。从谈判的角度来看,鉴于富裕国家在气候融资方面表现不佳以及其自身对煤炭的长期热爱,坚持煤炭是留给发展中国家的为数不多的谈判筹码之一。但格拉斯哥缔约方会议的决定是第一个点名提及化石燃料补贴的决定,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承诺最终逐步淘汰煤炭(Depledge 等人,2022)。在许多国家,逐步淘汰煤炭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项目,经常使环境正义与社会和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相互对立(Kalt,2021)。
2022 年的 COP27 也未能更广泛地讨论化石燃料问题,也未能呼吁“逐步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带头反对,欧盟和环保组织指责埃及会议主席国不遗余力保护石油国家和化石燃料工业(Kottasová等,2022)。据一种说法,至少有 636 名化石燃料游说者参加了 COP27,其中许多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他们将于 2023 年底担任 COP28 主席(Harvey & Michaelson,2022)。这让许多观察家对来年的缔约方会议进程感到担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与石油行业合作才能应对气候危机。对化石燃料补贴的政策改革并最终将不可燃烧的化石燃料留在地下,需要在社会、政治和工业利益之间取得谨慎的平衡,无论经济和制度发展阶段如何(Pellegrini & Arsel,2022;Jones & Cardinale, 2023)。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关于终结化石燃料的讨论已经认真开始,并且不会消失。
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赔偿
2022 年 COP27 上的头条突破是同意建立一个“损失和损害”基金,由发达国家的捐款提供资金。它涉及气候危机的公平和环境正义维度的核心(Agarwal & Narain, 1991 ; Timmons & Parks, 2009)。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这种专门的供资机制,这些国家在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中遭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而它们对此不负有责任。2022 年夏天巴基斯坦发生的灾难性洪灾有力地证明了贫困国家在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加剧面前的脆弱性。
如何应对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多年来一直被提上议程。2014年,COP19通过了“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其他活动包括圣地亚哥技术援助网络、斐济风险转移信息交换所以及格拉斯哥对话。这些活动均不包含任何资金(Puig,2022)。
当欧盟决定原则上同意这一想法,而美国最终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放弃反对时,建立独立于其他气候融资的专门“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倡议获得了关注。和民间社会组织(Plumer 等人,2022)。迄今为止,富裕国家一直反对这一要求,担心面临无限的金融负债。即将召开的气候会议仍需要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哪些损失和损害事件必须被视为与气候变化相关,谁应该有资格获得赔偿融资,以及谁应该向该基金付款?
欧盟坚称,该基金将仅用于援助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最终文本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也没有确定谁将提供融资,但它指出这些资源将是“新的和额外的”,并且“补充并包括”不属于《公约》和《巴黎协定》(UNFCCC,2022 年)。” 欧盟和美国坚持扩大捐助基础,将韩国、沙特阿拉伯、中国和新加坡等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纳入其中。目前,中国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在 COP27 的最后几个小时,谈判归结为保留格拉斯哥采用的 1.5°C 语言和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之间的权衡(Kottasová et al., 2022)。
长期融资
国际气候谈判背景下的经济补偿是各国之间更公平、更平等地分摊负担的关键,这些国家对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历史责任截然不同,应对其后果的社会经济能力也截然不同。但在全球社会契约的背景下什么构成“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上,各国仍存在很大分歧,该社会契约可以控制剩余碳预算的分配,使其保持在 1.5°C 以下(UNEP,2022a)。此外,许多捐助国在兑现其政府承诺的数额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COP16) 未能就 2012 年之前谈判的《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执行期 2012-2020 的途径达成一致,但它确实明确指出,应从公共和私人来源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到 2020 年,每年都会提供用于缓解和适应的资金(Clémençon,2010)。有多少来自公共来源,有多少来自私人来源,目前仍处于开放状态。经合组织显示,2020 年发展中国家为气候行动筹集了 833 亿美元,仍低于原定目标,但好于往年(经合组织,2022)。但早些年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涉及政府重复计算、政府拨款融资相对于商业私营部门流量的比例不断下降以及私营部门使用不一致的标准来确定什么应被视为“气候融资”的报告不透明。 (Westphal 等人,2015;Bhattacharya 和 Calland,2020)。此外,气候融资主要受益于亚洲和中等收入国家,而忽略了能源匮乏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减排潜力巨大(Michaelowa等,2021)。
气候正义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鉴于世界上最富有的 1% 人的碳排放量是最贫穷的 50% 人的总碳排放量的两倍,发达国家在经济补偿方面远远不够(Newell,2022)。仅最富有的 5% 人(所谓的“污染精英”)就贡献了 1990 年至 2015 年间排放增长的 37%。尽管全球碳排放量不到 4% 来自非洲,但非洲大陆经历了一些最严重的气候影响变化,温度上升速度比平时更快。
融资从一开始就是气候谈判的核心。全球环境基金(GEF)于 1991 年启动,是第一个为支持实施 UNFCCC 提供融资的融资机制(Clémençon,2006 年;2020 年)。但全球环境基金涵盖了其他全球环境公约,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多年来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的气候融资每年仅为 300-5 亿美元。2014年,专门成立了绿色气候基金(GCF),以满足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捐助者主导且资金不足的全球环境基金持批评态度的长期需求。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在 2024 年至 2027 年期间的财务承诺为 114 亿美元(GCF,2023)。
气候融资由三个部分组成:减缓、适应以及损失和损害的资金。迄今为止,通过多边渠道提供的大多数气候融资都是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即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来说,适应全球变暖是一个关乎生存的优先事项。2010 年设立了一个小型适应基金,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在内的多边银行承诺推动旨在提高各国气候适应能力的项目。但所追踪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缓解活动;适应仅占私人资金流量的 0.1%(CPI,2019 年)。
预计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将增加一倍,而目前 40% 的人口仍未接入电网。安全清洁能源对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至关重要。提供这种无碳能源将为缓解气候变化带来巨大回报,但需要的投资远多于目前可用的投资(联合国,2022)。2022 年 10 月,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 COP27 前媒体吹风会上,气候活动人士要求西方国家向非洲承诺提供 1.3 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Gichuku,2022)。
2022 年,世界银行集团提供 317 亿美元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世界银行,2022a)。由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气候怀疑论者大卫·马尔帕斯领导的世界银行因在优先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够而受到严厉批评(Hess,2021)。马尔帕斯此后辞职,为世行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以应对用太阳能和风能取代煤炭产能的巨大机遇(Harvey,2023;Michaelowa 等,2021)。
主要捐助国正在讨论大幅扩大世界银行能力的战略。该战略的一部分将针对私营部门,政府相信私营部门能够兑现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然而,私营部门在投资气候行动方面却有着不良记录,同时宣传其自愿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Clémençon,2021)。行业的动力可能最终会增强。一个标志是联合国召集的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 (NZAOA),这是一项由成员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倡议,致力于到 2050 年将其投资组合转变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2b))。这包括决策中的气候风险评估,以及对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中搁浅资产的财务责任的重新评估,如果世界认真对待1.5°C的情况,如果没有昂贵的碳捕获技术,这些资产将无法燃烧。
如何确保每年 4 万亿美元的长期全球气候投资的工作仍在继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短期内可能大幅扩大规模(IEA,2021)。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在生产或消费源头征收某种国际碳税——几十年来已经显而易见,但仍然没有机会找到所需的支持(例如,Selrod,1995;Clémençon,2000)。
30 年来多边气候谈判发生了哪些变化
1992年各国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世界上有50亿居民,但35%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22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但贫困率已降至10%以下(世界银行,2022a;2022b)。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过着更好、更长寿的生活,妇女和儿童也获得了比以往更好的经济和教育机会。伟大的脱碳项目旨在继续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时摆脱化石燃料。
影响应对挑战的机会的许多因素和趋势正在发生变化,最终可能使这一目标成为可能,并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气候科学已得到解决,气候否认主义已经减弱,气候正义青年运动已取得重大进展影响主要国家不断变化的选举结果,化石燃料行业作为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其错误信息策略的公开,政策制定者最近在诸如基于标记的工具之后变得更加支持直接排放法规碳税和排放交易未能发挥作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终于与化石燃料能源相比具有成本竞争力,并且其部署迅速增长。
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已经解决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1年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总结和分析了全球研究工作(IPCC,2021)。地球监测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实时地球物理信息和预警系统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可用。特别是,自 IPCC 于 1989 年发布第一份报告以来,人们对全球变暖如何在不同地区发挥作用的了解有了显着提高。
气候否认主义在 2000 年代初期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今天,基本的科学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例如,Oreskes,2010)。世界正在变暖并将继续变暖,而人为造成的温室气体就是原因(IPCC,202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呼吁进行更多科学研究是一种拖延行动的策略,许多科学家呼吁在政治进程对当前知识做出反应之前暂停开展另一次 IPCC 评估(Glavovic 等,2021)。2022 年在 19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 PEW 调查发现,气候变化是受访者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头号威胁,排在所有其他问题之前(Poushter 等,2022)。
充满活力的气候青年运动已将代际维度推向前沿和中心
几十年来,气候危机的代际和公平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旁注,现在终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8 年 15 岁瑞典女学生 Greta Thunberg 的个人行动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她的气候活动团体“星期五为未来”在世界各地的学童中赢得了追随者(FFF,2022)。青年激进主义在巴黎气候会议召开前几年就已经出现,由 305.org 等大学非政府组织领导,但之前从未发展出目前的政治影响力。
至少部分是为了缩小代际“热情差距”,候选人乔·拜登宣称气候危机是他在与现任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竞选中对美国总统的生存威胁(Milman,2020)。2021年,青年投票帮助德国绿党一跃成为2021年德国议会选举中的第三大党,并成为社民党总理奥拉夫·舒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重要联盟伙伴。
将气候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主要污染者
在科学研究的支持下,活动人士成功地改变了关于谁应对气候危机负责的说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主流说法是,气候危机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化石燃料提供了我们所有人都依赖的廉价而可靠的能源。人们有一种隐含的理解,即消费者需求驱动供应,而化石燃料公司只是满足需求。这种叙述非常适合该行业的战略,该战略现已有据可查,旨在破坏向可再生能源技术过渡的监管措施。转向可再生能源成本高昂且对普通消费者不利的观点强化了这一策略(Cho,2021)。
然而,最近的研究揭示了两个事实。首先,温室气体排放可归因于向世界提供化石能源的相对少数大公司和国家(McKibben,2012;Ekwurzel等,2017;Johnsson,2018),其次,跨国公司雇佣了化石能源。欺骗性策略破坏任何远离化石燃料的行为。
为了破坏科学发现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已经发起了大规模且蓄意的虚假信息运动(Oreskes,2010;Supran & Oreskes,2021;Williams 等,2022)。现在的记录显示,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公司几十年前就在内部接受了全球变暖作为一个科学事实以及对其公司基础设施的威胁。石油公司在政治运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选举立法者,反对任何减少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Mayer,2017))。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能体现这一点,最近一次国会听证会证明了这一点,该听证会产生了内部行业文件,显示了数十年来企业如何在绿色声明上欺骗公众(Green et al., 2021;Milman, 2022b)。
随着化石燃料行业的阻挠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在美国大学受到关注——针对养老基金和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大型投资者(Hestres & Hopke,2019)。近年来,荷兰和德国的诉讼认定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对造成气候危机负有责任(Ekardt,2022)。
公众已经认识到气候否认主义的一个关键根源,尽管这种转变在世界各地并没有统一发生。该行业的力量仍然强大,特别是在产油发展中国家,尽管它可能正在减弱。然而,直到 2021 年格拉斯哥会议召开之前,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呼吁从未成为会议决定。这是思维转变的一个微小但也许很重要的迹象。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局限性:碳税、排放交易和净零承诺
世界已经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接受碳税和排放交易可以有效取代严格的政府监管来应对气候危机的论点。这一推理符合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导政策方针,由美国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和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领导的保守派政府带头,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Harvey,2005)。
碳税
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被视为市场的免费投入。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直接监管往往在经济上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因为它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几乎没有给行业带来灵活性。如果环境被定价——通过污染费或税收——市场参与者就会找到最具成本效益的应对方式(O'Riordan 1997;OECD,1995)。私营部门迅速加入进来,赞扬此类政策工具原则上提供的灵活性,但经过多年的“研究这个问题”,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征收碳税,并且所有国家都免除了能源密集型出口部门(经合组织,2019);艾金斯和斯佩克,2000)。
反税收联盟很快就变得和反监管联盟一样蓄意阻挠。1992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提议,即在欧盟范围内征收碳税,以支持气候谈判,但这一提议毫无进展(Barnes & Barnes,1999)。在美国,一项对化石燃料的碳含量征税的能源法案很快在 1993 年被否决,1994 年的国会选举使共和党反税联盟上台。
经济理性论点还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未来将拥有净化环境的技术,因此目前不需要采取“昂贵”的措施来减少排放。将经济学家所谓的贴现率应用于气候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有意义的监管的延迟,特别是美国对碳税的反对(Nordhaus&Boyer,1999)。这种假设从来没有现实基础,而且事实证明在气候变化方面尤其具有误导性(Kysar,2010)。但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
碳定价的想法在理论上是引人注目的。但现在的历史表明,它忽视了政治阻力,同时破坏了对监管排放标准的支持。它导致了气候问题的极端两极分化,以及碳税必然惩罚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神话(Green,2019)。2000 年代初,很明显,无论是对能源部门的直接监管还是征收碳税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排放交易
随后讨论从碳税转向排放交易。排放交易将使工业界能够以最便宜的方式减少排放。如果一个参与者(国家或公司)能够将其排放量减少到超出法律要求的水平,它可以将多余的排放信用额出售给另一个市场参与者,而从源头减少排放的成本会更高。碳市场不言而喻的好处的循环推理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aterson & Stripple,2012)。为了挽救《京都议定书》,欧洲国家默许了美国的要求,即各国应能够通过相互交易排放信用额来共同实现全球目标。
在最后一刻,根据巴西的倡议,进一步明确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资金,并为自己申请由此产生的排放信用。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属于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清洁发展机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京都议定书》的完整性,但它也被视为补充全球环境基金(GEF)气候融资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能力的一种方式开发碳减排项目(Fuhr & Lederer,2009;Friberg,2009)。
当《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生效时,欧盟建立了排放交易计划 (ETS),涵盖欧盟 14,000 多个行业(Skjærseth & Wettestad,2008 年;Oberthür & Pallemaerts,2010 年))。排放交易的复杂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需要复杂的基础设施和方法来衡量、验证和最终证明减排量,以便能够颁发可交易的经认证的减排量证书(CER)。但最重要的是,这取决于政治决策,将总体排放上限设定到一定水平,从而为投资产生二氧化碳减排信用创造明确的激励措施。ETS 中碳信用额的价格很快从推出时每吨二氧化碳 35 美元左右暴跌至 6 美元,消除了企业投资减排的任何动力(Wettestadt 2014)。此后,欧盟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已开始稍微改善这一情况,但事实证明,碳排放交易往好里说作用有限,往坏里说只是一个旨在破坏严格监管的特洛伊木马(Markard & Rosenbloom,2020)。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可再生能源、排放和能源效率目标相关的具体法规来补充排放交易体系(Lindberg,2019)。欧盟将其可再生能源技术目标从 2030 年的 32% 提高到 45%,德国在 2021 年决定到 2030 年逐步淘汰煤炭并达到 80% 的发电量,并不依赖于排放交易(Klingert,2022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有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丹麦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和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开发商的所在地,计划到 2027 年电力消耗 100% 基于可再生能源。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消耗和生产的供应方措施也终于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性丹麦和德国都设定了到 2030 年逐步淘汰煤炭的明确期限(Pellegrini & Arsel,2022)。
许多强制性的区域、国家、地方和自愿排放交易体系现已投入运行。但规则不同,由此产生的排放信用额的价值也不同。前两届缔约方会议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京都议定书》CDM机制下获得的各类核证减排量(CER)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入巴黎后的NDC,或者会议术语中所说的“CER”。 “国际转移缓解成果 (ITMO)”(IISD,2022b,第 17-18 页)。相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集中会计和报告平台报告和跟踪各种类型的 CER 和 ITMO。
净零承诺
在 2022 年 COP27 之前,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79% 的 88 个国家已采用净零目标(环境署,2022a)。净零承诺依靠排放抵消来抵消实际排放量,而实际排放量无法减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重新造林或森林保护项目相关的排放交易。但据一些人估计,要使世界实现净零排放,需要重新造林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巴西的面积(Cho,2021)。原住民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将土地使用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碳抵消计划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土地掠夺,而对重新造林土地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到 2050 年粮食价格上涨 80%(Dabi & Sen) , 2021)。净零承诺也可能依赖于尚未开发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碳捕获技术。但净零排放承诺的可信度和可行性仍然非常不确定,无法弥补直接针对化石燃料行业提供供给侧政策的需要(McKibben,2012;Watt,2021;Pellegrini & Arsel,2022)。
在最近召开的缔约方会议之前,各国根据难以比较的各种基准提出了一系列承诺。芬兰是一个森林广阔、人口稀少的国家,其目标是到 2035 年实现净零排放。冰岛和奥地利的目标是 2040 年,德国和瑞典的目标是 2045 年。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目标是2050年,而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等一些国家的目标是2060年;印度已承诺到 2070 年实现净零排放。在做出净零排放承诺的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法国、德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少数国家(包括瑞典、丹麦、法国、德国、英国和新西兰)合法地实现了净零排放。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气候政策追踪,2023)。
私营部门也做出了净零承诺。但很少有人包括其价值链产生的排放量。除非对此类私营部门的承诺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严格监督,否则不能只看其表面价值( Williams 等,2022)。这种讨论非常类似于私营部门首先支持碳税和后来的排放交易的想法,结果证明这主要是一种推迟监管的策略。
显然,如果没有碳抵消,各国将无法实现深度脱碳。因此,国际进程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帮助澄清与排放交易和零排放方法相关的许多问题。但它无法回避一个大问题,即除非出现具有成本效益的碳捕获技术,否则抵消机会非常有限,这将为国际合作提出新的挑战(Maher&Symons,2022))。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也不能成为推迟实施与 2030 年大幅减排相一致的决定性实际减排政策的理由。
总之,在碳税和排放交易等所谓的基于标记的激励方法未能实现承诺的减排之后,许多国家正在回归旧式监管。他们正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目标,并采用源头和供应方的具体标准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流行政治哲学中姗姗来迟但意义重大的转变。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市场成熟
过去几十年来,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达到市场竞争力。但能源方面有两个故事情节:第一个是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大大超出了预期,第二个是世界继续严重依赖和投资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缓慢起步之后,受到全球政府大量补贴支持的低化石燃料价格的阻碍,终于实现了市场可行性,并且在过去几年中的扩张超出了预期。2020 年和 2021 年,包括风电场和太阳能项目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交付量增长了 45%(IEA,2022)。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2022 )的数据,2021 年新安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中近三分之二的成本低于世界上最便宜的燃煤发电。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考虑到所有成本,美国 99% 的燃煤电厂的运营成本高于可再生能源项目( Solomon 等人,2023 年))。中国、欧洲、美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目前引领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需求。例如,2022 年 12 月,越南同意与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领导人达成一项 155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协议,以摆脱煤炭,此前印度尼西亚最近与印度尼西亚达成了 200 亿美元的融资协议,以增加清洁能源并逐步淘汰煤炭(Kottasová) ,2022)。
俄罗斯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导致政府支出增加超过 5000 亿美元,以支持全球清洁能源(Lehnis,2022)。IEA 预计,到 2030 年,这将成为动员私人投资每年超过 2 万亿美元进入清洁能源的催化剂,但仍远低于 IEA 认为世界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 4 万亿美元 ( IEA , 2021) 。对于太阳能和风能来说,未来五年平均年新增发电量将需要几乎是目前预测的两倍。脱碳的最薄弱环节是建筑物的发热。一些欧洲国家大幅增加了对热泵的财政支持,但此类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能源故事中令人警醒的部分是,迄今为止,化石燃料仍然是世界上的主要能源,并且在全球中产阶级迅速增长的推动下,需求持续增长。几十年来,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一直居高不下,约为 80%(IEA,2022)。各国仍在推进日益受到环保组织攻击的“碳炸弹”项目(LINGO,2023)。到 2022 年,全球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和开采投资将超过 1 万亿美元(IEA,2022)。“五巨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利润合计达 2000 亿美元,令许多政府和公众感到震惊(Milman,2023 年))。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行业仍然存在巨大的政治利益,仍需要克服(Ekwurzel 等人,2017 年;Johnsson 等人,2018 年)。如何在不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将大量剩余化石燃料留在地下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Newell&Simms,2020)。
可再生能源和必要的电网更新的重大投资障碍也仍然存在。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绿色能源转型成本高昂,并且继续影响着企业和个人对能源转型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大多是错误的(Way 等人,2021)。此外,IEA 的世界能源模型等模拟模型无法捕捉技术成本改进趋势。更新预期以更好地符合历史证据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各国政府有关气候政策的辩论,并加速全球能源系统脱碳的进展,有望实现数万亿美元的净节省。
国际气候谈判的未来
美国和中国的排放量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 43%,而欧盟仅占 11%(气候政策追踪,2023 年)。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两国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都没有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也都没有承诺到 2030 年大幅减排和到 2050 年将净零排放保持在 1.5°C 以下(气候政策追踪,2023 年) 。
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分化的民主国家,历史上针对化石燃料的政策一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和依赖这些利益集团为选举融资的政客的一致抵制。中国是一个不自由的一党制国家,目前仍在继续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两国从根本上都互相指责对方做得不够,但两国都在国内采取重要措施来减少排放。很难看出他们如何克服各自对过去和现在排放轨迹的全球责任的根本分歧,从而为未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协议打开大门。其他极其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印度和巴西,
美国
美国对历史二氧化碳排放量负有最大责任,约占总量的20%,并且仍然是人均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是欧盟的三倍,是严重依赖煤炭的中国的两倍(碳简报,2021)。鉴于敌对和两极分化的国内政治背景,长期以来,它一直未能在气候政治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几十年来,从 1992 年里约会议开始,美国在推动气候谈判取得进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有目标和时间表的《京都议定书》到建立在自愿承诺基础上的《巴黎协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美国整个社会不愿意承担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历史责任并加入欧盟。引领世界经济脱碳。美国为许多其他国家提供了掩护,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对任何远离化石燃料的举措。莱格特,2001)。为发达国家制定强制性目标和时间表的《京都议定书》并没有失败,因为它是一项存在根本缺陷的协议,正如许多美国人现在所希望的那样。美国国会对《京都议定书》的敌意常常被认为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被视为搭便车者。但话题背后的原因始终是国内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该行业对政治运动的支持及其虚假信息策略的腐败影响(Oreskes & Conway,2010;Skocpol,2013;Mayer,2017)。
2022 年 8 月 16 日,美国国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法案,提供大量资金(3700 亿美元)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Paris 等,2022)。《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以纯粹的党派投票和大幅削减的形式获得通过。它的重点是为可再生技术创造税收抵免激励措施,特别是推动国产电动汽车的销售,其中包括支持开发碳捕获技术和扩大核能等。作为使该法案获得批准的政治让步,它也为化石燃料行业带来了好处。由于扭曲贸易的补贴有利于美国工业而不是外国竞争,这引起了贸易伙伴的担忧(布伦金索,2023)。
拜登总统克服重重困难推动美国气候议程值得赞扬。但在他出席沙姆沙伊赫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大多数国家和环保活动人士对这个最富裕国家迟来的、不充分的反应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气候活动人士却给美国冠以“巨大化石”的称号,因为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行星加热气体排放国(Milman,2022c)。埃及缔约方会议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 2023 年预算,其中仅包含拜登承诺的 2024 年气候融资 114 亿美元中的 10 亿美元( Milman,2022a),这对美国的立场没有帮助。
中国
自200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排放量增长迅速,已达到美国总体排放量的3倍左右,但按人均计算仅为美国的50%左右。近年来,中国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来减少排放,因为它认识到自己对气候变化的巨大脆弱性(Finamore,2022)。2015年《巴黎协定》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2020年,习近平主席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他承诺中国将停止在国外建设燃煤电厂(气候政策追踪,2023年))。然而,尽管中国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目前占全球总量的35-40%并且增长迅速,但该国还在继续扩大煤炭使用量。然而,由于经济放缓和新冠疫情封锁,排放量最近已趋于平稳(Myllyvirta,2022)。中国政府推出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经济问题,这也将有利于清洁能源投资。其影响将决定中国的排放量是否已经达到峰值,或者在本十年晚些时候达到峰值之前是否仍会反弹。
中国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还面临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压力,因为中国拒绝支持符合1.5℃巴黎目标的具体全球2030年减排目标。中国被指控动员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反对这种措辞,并暗中威胁要扣留基础设施资金(Kottasová et al., 2022)。然而,关于中国应如何积极减少煤炭使用的争论也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中国的气候科学家和政策顾问希望实施更严格的排放限制,而强大的省份和行业团体则不希望这样做(Finamore,2022) 。
中美对话仍然是气候谈判背景下最重要的外交途径。美国外交在2016年中国同意签署《基加利议定书》以减少氢氟碳化合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氢氟碳化合物是一种消耗臭氧层物质,属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管辖范围,但作为温室气体的作用更为强大。同样,在格拉斯哥会议上,在美国和欧盟的斡旋下,一些国家达成了一项附带协议,即到 2030 年将甲烷这一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Depledge 等,2022)。
欧盟
相对而言,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措施相关的最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仍然来自欧洲国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广泛社会共识和相对支持性的比例代表政治制度(Oberthür&Pallemaerts, 2010;奥贝图尔,2016;克莱门松,2016)。基于之前对抗空气污染和酸雨的斗争,并且长期高度依赖外国能源,它们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推动快速脱碳所需的政治步骤。乌克兰战争使更加顽固的东欧依赖煤炭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更加与北方国家的气候进步集团保持一致。
虽然美中关系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但历史上为各国气候行动奠定了基础的是欧盟(以及目前已脱离欧盟的英国)。欧盟超额完成《京都议定书》设定的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减排至少55%、到2050年成为第一个气候中和大陆的计划。在波兰获得减少对煤炭依赖的财政担保后(欧盟委员会,2023)。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于 2023 年 1 月提出了一项绿色协议工业计划,旨在通过简化监管、加快融资渠道、提高技能以及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来增强欧洲净零产业的竞争力。新的贸易协议。该提案将从现有欧盟基金中提供 2500 亿欧元(2720 亿美元)用于工业绿色化(Blenkinsop,2023 年)。
结论
气候危机正在显现。世界已经感受到比工业化前时期变暖 1°C 的影响,现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更广泛的进一步变化,包括到 2100 年海平面上升 2-3 英尺,以及更频繁、更强烈的热浪和洪水事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1)。这是由于气候否认主义、对市场机制毫无根据的信任以及化石燃料行业无耻地利用政策失败而拖延了二十年的代价。化石燃料行业赚取了数万亿美元的利润,而全世界数百万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价格。多边气候谈判未能果断应对这一问题,其相关性正在下降。
然而,我认为这次失败也有一线希望。现在的希望不是气候谈判取得突破,而是希望许多与国际气候谈判没有直接关系的趋势开始指向正确的方向。结论是,各国不能等待未来几年达成全面的全球气候协议。拥有有利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广泛公众支持的国家必须在国际层面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在这些积极趋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加强这些趋势。无论国际层面能取得什么进展,都将取决于他们的领导力和强大的气候行动俱乐部。
多边主义面临日益严峻的全面挑战。气候谈判存在适得其反的因素,因为它们被视为一场由大国赢得的游戏。在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累积的历史责任、当前责任和未来责任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满足美国、中国和印度的谈判立场,在目前条件下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考虑到紧张局势。国家压力,要求不要被视为向对手屈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只会增加商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以接替2015年《巴黎协定》的难度。
然而,国际气候谈判在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科学合作努力、强调气候危机的规范公平性、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为制定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奠定制度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他们以各种方式鼓励和帮助资助国家一级的气候行动,特别是在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并间接鼓励可再生技术的开发和采用。
我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国际气候合作的高潮。正是《京都议定书》及其硬目标和时间表引发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国家级能力建设,也许最重要的是欧盟于 2005 年试点的强制性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采用灵活性即使排放交易没有像所倡导的那样实现,但需要建立与衡量和核实排放基线以及减排努力相关的复杂实施机制的措施涉及广泛的政府机构、研究型大学、智囊团和私营部门实体。无论好坏,直接监管都不需要这种广泛的参与。C40 城市,2023 年; Mazmanian 等人,2020)。
2015 年《巴黎协定》尽管具有非约束性自愿性质,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垫脚石。自愿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反映了各国在制定基础广泛、详细的气候行动计划以推动国家讨论方面取得的进展(UNFCCC,2023)。不幸的是,这些国家自主贡献只能对一国过去的承诺与其当前的行动进行比较。由于国家自主贡献中使用的基线和目标年份不同,跨国比较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显示许多富裕国家的雄心不足(ClimatePolicyTracker.org)。总体而言,国家自主贡献中制定的当前政策意味着气温上升约2.8°C,距离《巴黎协定》所采用的1.5°C目标仍相去甚远。
只有对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重组,才能对气候危机做出决定性的反应,这需要采取贸易措施来帮助先行国家维持其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目标,以应对外国的肮脏竞争。20世纪90年代碳税的教训表明,如果仅限于国内市场,供给侧政策措施仍然无效。多边主义总体上面临的挑战为在贸易措施支持下更加毫不掩饰的单边气候行动主义提供了机会。但随着国际贸易体系陷入危机,任何全球贸易规则的振兴都必须在考虑气候政策的情况下进行修订,同时还要避免贸易战不断升级(Low,2022); 斯旺森,2023 年 1 月 25 日)。关注特定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政治敏感性似乎很大(Leonelli,2022)。如果没有明确修改贸易规则以支持到 2030 年全球大幅减排,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C 的目标很难得以维持。
各国新的产业政策越来越注重让工业更接近风能和太阳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中心,而这些中心往往远离当今的工业中心(《经济学人》,2023)。未来的绿色竞争力将取决于谁能够并且将利用这些机会,这需要大量投资并具有潜在的巨大回报。较少讨论的方面是,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在脱碳世界经济中竞争,从而加剧现有的不平等(Machin,2019;Pellegrini & Arsel,2022)。因此,融资仍然是支持更加公平地走出碳时代的过渡的核心。
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主要经济体已经采取了单边措施来支持加强国内气候政策——尽管它们对贸易的影响截然不同,需要与贸易伙伴进行更好的协调。绿色世界经济的竞争有望鼓励其他国家效仿,以避免失去重要的外国市场,并扩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目标。
国际气候谈判作为协调研究和整理许多方法、技术和流程相关问题以支持国家加强努力的论坛仍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向富裕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扩大气候融资,以缓解、适应、损失和损害。新兴碳抵消技术能够而且应该发挥的作用也将日益成为需要指导和协调的问题。气候危机是所有国家面临的生存挑战。如果那些主要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而能够这样做的国家继续推行正确的政策而不考虑国际层面发生的情况,那么所有的希望都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