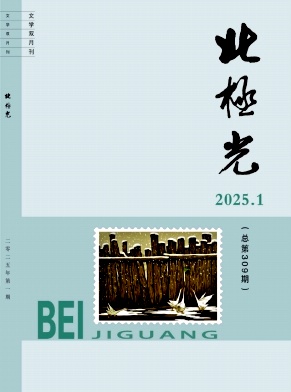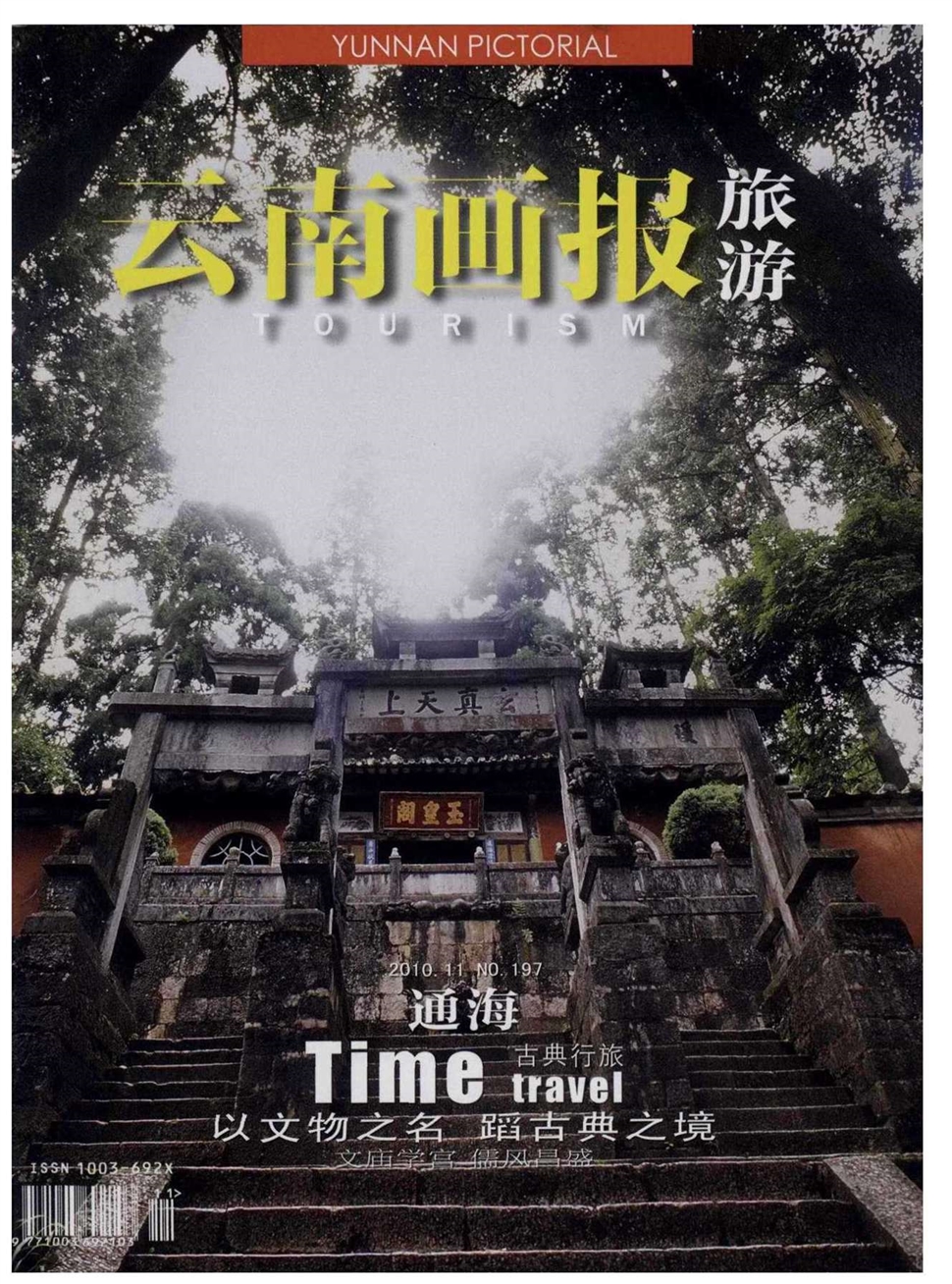新闻资讯
介绍
理解再分配的差异和发展是福利国家研究各个学科的一项重大任务。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相应理解取决于用于研究再分配的数据的稳健性。然而,我们用来分析再分配的数据实际上显示了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因为它在与“因变量问题”相关的文献中得到了重点讨论(参见Clasen 和 Siegel,2007;Otto,2018)。一般来说,文献区分了通常所说的产出(指法规或正式福利机构)和结果,例如导致有效不平等的结果(Green-Pedersen,2007))。
这种区别是再分配研究的前提,因为再分配法规中规定的其产出不一定与其结果相同。相反,各种原因使我们可以预见到,受监管的再分配会不平等地转化为再分配结果。相应数据的差异是由于未领取福利(Hernnz et al., 2004)、(不)使用税收法规和所谓的贝塔错误而导致的福利高于预期(Goedemé 和詹森斯,2020)。了解这些差异的程度使我们能够确定再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按规定发挥作用,以及实际的再分配与社会正式商定的差异有多大。这再次有助于理解意外的再分配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再分配对象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然而,关于一般再分配和特别是与家庭有关的再分配的研究(即本文的实证重点)往往没有考虑到这种差异。事实上,他们经常在分析设计中混合再分配法规和结果。在此背景下,我们的论文探讨了再分配结果与再分配法规的对应程度如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使用创新的分析方法。我们研究了作为再分配调节代理的一定总收入的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与作为相应再分配结果的相同总收入的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偏差。为此,我们使用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 (EU-SILC) 的数据,并使用欧盟税收优惠微观模拟模型 (EUROMOD) 模拟可支配家庭收入。为了考虑家庭的复杂性,我们比较了研究结果,以确定 20 种家庭类型(包括单亲家庭和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不同的夫妇)实际和模拟可支配家庭收入之间的差异。我们对七个欧洲福利国家(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芬兰、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了这项分析,因为它们的数据特别适合评估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借此,我们为再分配研究中的方法论辩论、欧洲比较中对再分配的理解以及对被忽视的不平等现象的识别做出了贡献。
本文的结构如下:下一节讨论有关再分配的文献以及法规和结果之间的差异。第三部分介绍了分析方法以及数据和方法。第四部分介绍了我们分析的实证结果。这些将在第五部分中讨论,本文的结论将在第六部分中提出。
最先进的
当前社会秩序的一大特征是再分配(OECD,2021)。因此,它也是最相关研究中两个最基本争论的核心。第一个涉及“再分配悖论”(Korpi和Palme,1998),分析社会再分配与福利国家机构设计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对不同收入水平公民的再分配,以及再分配对贫困的影响。 。Korpi 和 Palme(1998)得出的结论是,与那些拥有强大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相比,注重有针对性的福利的国家的特点是不平等和贫困程度更高。这两项发现都受到了严格的讨论(Gugushvili 和 Laenen,2021)并被最近的调查证实(Jacques 和 Noël,2018)。围绕再分配的第二个基本争论涉及更为突出的“福利制度”研究。通过应用去商品化的概念,Esping-Andersen(1990)启发了一系列文献(参见Emmenegger 等,2015),旨在捕捉发达社会中典型的国家-群体再分配逻辑。这些去商品化研究采用了与Korpi 和 Palme(1998)类似的再分配观点,重点关注工作公民和非工作公民(例如养老金领取者或失业者)之间的再分配。
尽管这些研究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但它们在再分配方面都存在盲点;他们没有考虑家庭方面的重新分配。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所有主要福利国家研究都阐述了(但没有系统分析)家庭在理解再分配方面的相关性(例如参见Frericks,2023;Esping-Andersen,1990;Marshall,1950),而且事实上,所有欧洲社会都已将与家庭相关的福利和财务义务制度化(Frericks 等,2016)。家庭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非家庭化的概念来研究的。根据李斯特 (1994:37),这个概念描述了“独立于家庭关系的成年人个体能够维持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程度”。因此,它关注女性的经济独立以及家庭和照料政策与性别相关的影响(Leitner,2003;Zagel 和 Lohmann,2021)。然而,去家庭化的概念在分析与家庭相关的再分配时是有问题的。首先,将一维视角应用于家庭,因为该概念不区分家庭类型(Saxonberg,2013)。其次,陌生化研究在调查福利政策的社会影响时,在其分析设置中混淆了法规和结果(例如Leitner,2003; 罗曼和扎格尔,2016)。此外,结果受到非监管因素的影响,例如偏好,而这些因素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这种方法论问题在再分配悖论的研究中同样普遍存在(参见Jacques 和 Noël,2018;Korpi 和 Palme,1998)。不过,明确区分法规和结果对于理解再分配很重要。只有明确区分,我们才能确定社会正式同意的再分配,以及立法上的再分配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所发现的差异揭示了再分配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预期结果。这与概念和社会原因相关。首先,关于再分配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差异方面的再分配(参见埃斯平-安德森和迈尔斯,2009)。区分法规和结果将有助于在再分配方面建立更正确的国家分组,因为广泛认可的政权类型可能不像一般假设的那样依赖于政策设计,而更多地依赖于整体社会差异(Frericks,2021)。其次,当再分配法规和结果之间的差距因仅限于特定社会群体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时,它就具有社会相关性。此外,当决定的再分配与其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时,单一法规或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也面临危险(Eurofound,2015))。出于这些原因,本文讨论了再分配结果与再分配法规的对应程度如何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填补上述方法上的空白以及家庭再分配方面与内容相关的研究空白。由于不同家庭类型的再分配规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将研究各种家庭类型(Frericks et al., 2016 , 2023)。因此,所规定的再分配与结果中确定的再分配之间的偏差被认为因家庭类型而异。
期望在再分配方面发现法规和结果之间的差异有多种原因。福利金作为再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资格享受福利金的个人或家庭并未获得,因此实际收益可能低于预期。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广泛讨论为不接受。从广义上讲,不接受的原因在于客户、管理和福利计划层面(van Oorschot,1998;Vinck 等,2018)。此外,金钱决定因素、信息成本和行政流程的延误也会影响不接受(Hernanz 等人,2004 年))。考虑到家庭类型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收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有移民背景的家庭的不接受程度最高。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对资格了解较少,并且成功申请福利更加困难(Janssens 和 van Mechelen,2022)。此外,拥有较多子女的家庭更有可能不接受,因为他们需要更频繁地申请(可能不同的)与子女相关的福利。
相反的现象,即个人或家庭获得的资源高于法规规定的资源,被称为贝塔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由于管理程序错误或欺诈造成的,但测量错误也可能导致贝塔错误(Goedemé 和 Janssens,2020)。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贝塔误差是否与个人或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相关。
此外,税收和社会保险缴款(SIC)在再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家庭缴纳的税款和 SIC 可能高于预期,这可能是由于未使用扣除额所致。与不领取福利类似,信息成本和有关申请流程的知识也是相关因素;因此,我们假设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缴纳的税款高于预期。其次,由于欺诈等原因,个人或家庭缴纳的税款和证券投资税也可能低于法规规定。根据我们的分析,收入少报被认为是税收和 SIC 方面结果与法规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OECD,2019),其他研究则指出了相反的方向(Dayıoğlu Erul,2021)。一般来说,税收士气很难与社会经济特征联系起来。
根据这三个解释因素,我们假设再分配结果和法规有所不同,并且它们因家庭类型而异,因为这些家庭类型的福利资格和纳税义务不同(参见Nelson 和 Nieuwenhuis,2021)。根据现有文献,结果和法规之间的差异将对收入较低和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产生负面影响。还可以假设法规和结果之间的偏差存在跨国差异。关于逃税和纳税士气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跨国差异。然而,虽然使用汇总数据的国际研究显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纳税合规性之间的关系,但使用欧洲微观数据的研究并未呈现出不同国家的区域或经济差异的明确模式(参见Kukk 等人,2020)。关于(不)领取福利金的研究通常涉及单一福利并研究单个或少数国家案例(例如Fuchs 等人,2020; Vinck 等人,2018)。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很难期望反映国家差异的具体模式。因此,针对国别差异,我们的研究采取了探索性的方法。
方法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解释我们的分析方法、我们使用的数据以及我们用于回答研究问题的变量和方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这个研究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我们的分析方法,这将在下面的方法部分中具体化。再分配的相关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是总收入,如福利国家再分配的研究(Esping-Andersen和Myles,2009)、同工同酬和性别工资差距(O'Reilly等,2015)。然而,除了法规之外,总收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偏好、行为或劳动力市场结构(Bowles 等人,2001 年;欧盟统计局,2020 年;Pfau-Effinger,2005 年))。因此,只有当整体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秩序被视为等同于其再分配规则时,总收入的差异才能为再分配提供见解。这个方程经常被发现(例如Daly,2020),并且大多没有反映其概念、方法论和经验断层线(如现有技术和Frericks 等人,2016中所讨论的))。相比之下,净收入则通过福利、税收和 SIC 直接受到再分配法规的影响。因此,我们采用模拟净利润——即在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模拟——来研究监管下的再分配。再分配结果以实际净收入来衡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轻松确定受监管的再分配和再分配结果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的总收入与它们的来源相同。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家庭方面的再分配,因此我们研究了家庭的模拟和实际净收入。家庭的模拟净收入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类型方面的受管制再分配,包括影响所研究家庭的所有相关再分配法规,而家庭的实际净收入代表了家庭类型方面再分配结果的充分指标。通过测量总收入相同的家庭类型的实际净收入和模拟净收入之间的差异(Δ)来确定监管再分配和再分配结果之间的差异。
为了将家庭作为一个多维概念进行研究,不仅从社会学角度,而且从再分配法规的角度,我们区分了多种家庭类型。首先,有些家庭有或没有受抚养子女。家庭的一些定义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解释为将社会单位称为家庭的前提(Schneider 和 Kreyenfeld,2021)。然而,我们采用了更广泛的定义,将没有孩子的夫妇包括在内,因为再分配法规也将他们视为一个家庭。出于逻辑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调查仅限于正式登记的家庭类型,因为法规无法直接处理未知的家庭成员。为了涵盖儿童数量的足够变化,我们考虑了家庭是否有 0 到 3 个或更多的孩子。不同家庭类型的第二个相关特征是单亲家庭还是夫妻家庭。最后,作为第三个特征,我们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家庭类型的再分配,因为如上所述,再分配规定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取决于收入水平。
数据库
为了分析实际和模拟净收入,我们使用了欧盟税收优惠微观模拟模型(EUROMOD)中的输入数据。该数据集基于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数据 (EU-SILC)。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确定 EU-SILC 中报告的实际净收入,并借助 EUROMOD(版本 I4.109+)(ISER,2022)模拟净收入。
在我们的横断面分析中,我们使用了 2020 年以来最新的 EUROMOD 输入数据。由于该数据集中的收入变量指的是上一年(即 2019 年),并且 2019 年收入受到 2019 年法规的影响,因此我们利用了法规数据从 2019 年开始。因此,我们的分析并未受到 COVID-19 大流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了确定再分配法规与结果之间偏差的跨国差异,我们的分析包括七个欧洲国家。这一选择是基于 EU-SILC 中有关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的登记数据的可用性(以及 EUROMOD 输入数据)。这保证了对再分配法规和结果之间偏差的最合理的计算。更常用的基于调查的收入数据可能会偏离“真实”收入数据。提供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芬兰、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注册数据。瑞典、芬兰和荷兰属于“老”注册国,它们几乎完全使用 EU-SILC 中的注册数据(Törmälehto 等人,2017 年))。奥地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最近转向使用登记数据,因此尽可能使用此类数据,因为每个国家的行政数据并不包含完全相同的变量(Törmälehto 等人,2017 年;Zardo Trindade)和戈德梅,2020)。
我们研究的样本由所研究的家庭类型的家庭组成。我们排除了接受社会援助福利的家庭类型,因为此类福利的不接受率非常高(Fuchs et al., 2020),而接受全额社会援助的家庭通常不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保险。这可能导致我们对低收入家庭类型的调查结果出现偏差。为了纠正选择偏差的概率问题,我们使用了 EU-SILC 数据中提供的家庭横截面权重。表 1总结了每个国家的未加权和加权家庭总数。
变量和方法
我们根据实际和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研究了实际和模拟净收入。在我们的分析中,中心利益变量计算为实际和模拟可支配家庭收入之间的偏差。它的计算方法是 EU-SILC 数据 (yds) 中报告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减去基于 EUROMOD 微观模拟的模拟可支配家庭收入 (ils_udb_yds)。表 2列出了实际和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组成部分。对每个家庭得出的变量进行了总结,并以购买力平价 (PPP) 形式给出,以便进行跨国比较。
为了对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更详细的调查,我们分析了实际福利和模拟福利以及税收和 SIC 之间的偏差。这使我们能够了解,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家庭类型,实际和模拟的可支配家庭收入之间的偏差是否是由于可支配家庭收入的相同或其他因素造成的。实际和模拟税收和 SIC 之间的偏差计算为 EU-SILC (tis) 中报告的税收和 SIC 减去基于 EUROMOD (ils_udb_tis) 微观模拟的模拟税收和 SIC。为了调查实际福利和模拟福利之间的偏差,总结了所有福利,并在数据中以模拟和非模拟变量的形式提供。这保证了实际效益和模拟效益的变量的可比性。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税收和 SIC 的构成,另一方面福利的构成因国家而异。因此,实际和模拟效益以及税收和 SIC 的变量在国家内部以相同的方式构建,但国家之间则不然(参见在线附录中的表 A1 和 A2)。
为了研究家庭类型之间的差异,我们根据 EU-SILC 数据中提供的等值可支配净收入区分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在这里,我们使用等值的可支配收入,因为它通常是区分不同收入群体的基础(例如在研究贫困时)。根据通用定义,收入低于中位数 60% 的家庭面临贫困风险,可被定义为低收入家庭(欧盟统计局,2022 年)。中等收入家庭的可支配净收入在中位数的 60% 到 150% 之间。最后,收入至少为中位收入 150% 的家庭被定性为高收入家庭(有关收入群体的阈值,请参见经合组织,2020)。
要分析不同的家庭类型,调查一个家庭的住户类型至关重要。出于方法上的原因,我们需要假设一个家庭住在一个家庭中。我们的分析中有七种家庭类型:有一个、两个和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单亲家庭;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以及一对有一个、两个和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夫妇。在有子女的家庭类型中,我们仅考虑有 18 岁以下受抚养子女的家庭,这也是出于方法上的原因。此外,我们在分析中排除了拥有三个或以上孩子且高收入的单亲家庭类型,因为他们是数据中明显的异常值。
考虑到家庭收入和家庭类型变量,我们总共区分了20种家庭类型。为此,我们通过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不同家庭类型的偏差程度,而不是根据其特征来解释偏差,因此多变量方法被认为是不够的。
我们的数据库和方法的一些局限性必须得到解决。尽管 EUROMOD 提供了对福利、税收和 SIC 的非常准确的模拟,但某些案例可能缺少有关经济状况调查福利和税收减免的资产测试信息,从而导致福利金额和税收的高估(Maier 和 Ricci,2022 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值和模拟值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 EUROMOD 中的模拟错误造成的。不幸的是,无法根据现有数据量化此类错误。
发现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介绍实际和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平均偏差的研究结果。我们在下一步中分析我们的发现,以确定实际和模拟税收和 SIC 之间的平均偏差,以及实际和模拟效益。这有助于我们确定实际和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来自何处。
首先,我们列出了所有家庭类型的标准差(SD)以及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偏差平均值(表3))。奥地利、西班牙和瑞典的平均值相对较低(瑞典是唯一一个负值的国家,即平均实际收入低于模拟收入)。在这些国家,模拟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几乎没有偏离实际收入。这种偏差在芬兰、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更为明显,尤其是在荷兰,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模拟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平均偏差超过 500 PPP。荷兰的标准差也最高(1363.34),这表明 20 种家庭类型之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模拟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偏差存在很大差异。
图2事实表明,实际的可支配家庭收入确实与模拟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存在差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显着差异。比较反映不同家庭类型的三个收入群体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偏差的程度和方向存在显着差异。但我们也清楚地观察到,除了两种例外(西班牙有一个孩子的单亲家庭和拉脱维亚无孩子夫妇)外,低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低于模拟收入。这在奥地利最为明显,但斯洛文尼亚、瑞典和芬兰的低收入家庭类型也表现出相当高的负偏差,而在拉脱维亚最不明显。相比之下,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类型,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结果发现,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高于模拟家庭收入。这种情况在荷兰最为明显,但在芬兰、拉脱维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类型)也是如此。对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类型,瑞典和西班牙的偏差最小。奥地利、瑞典和西班牙是特例,部分中高收入家庭类型呈现负偏差。
税收和 SIC 的调查结果(图 3)显示出清晰的负偏差图。请注意,这种负偏差导致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高于模拟家庭收入。总体而言,高收入家庭类型的负偏差最高,而低收入家庭类型的负偏差最低。我们发现荷兰、芬兰、奥地利和拉脱维亚的高收入家庭类型负偏差最高。奥地利又是一个特例,因为所有低收入家庭类型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类型支付的实际税款和 SIC 比模拟的要高。这种偏差的程度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在瑞典,七种低收入家庭类型中的四种(以及一种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的实际税款和 SIC 高于模拟,但程度低于奥地利。
关于福利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家庭类型收到的福利金比模拟的要少(图 4)。这在低收入家庭类型中最为明显。我们发现奥地利的值最高,其中负偏差随着儿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类似于税收和 SIC)。斯洛文尼亚的负偏差也相当高。芬兰和瑞典的结果与这些结果相反。在这里,一些家庭类型,特别是中高收入家庭,获得的实际福利高于模拟。拉脱维亚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福利方面总体偏差最小的国家是西班牙和拉脱维亚。同样,荷兰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类型的偏差也较小。
讨论
衡量受监管的再分配与再分配结果之间的偏差,可以让我们了解再分配与社会正式达成的共识有多大程度的对应,以及最终谁的境况实际上更好或更坏。我们的结果显示,总收入相同的家庭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与模拟可支配家庭收入的对应程度因家庭类型和国家而异。
从家庭类型来看,不同收入的家庭类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通常低于模拟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即他们从各自的再分配法规中获得的收入低于预期)。文献表明,这些家庭往往缺乏关于是否以及如何申请福利(van Oorschot,1998)或如何利用税收减免的知识。这对于高收入家庭类型来说是不同的,在大多数国家,中等收入家庭类型也是如此: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高于模拟收入。这似乎是马太效应的一种变体——穷人比中产阶级获得的资源更少(Gal,1998)。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还取决于它们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
我们的研究结果得出的另一个普遍见解是,一方面,福利,另一方面,税收和 SIC 与家庭可支配总收入的相关性是不同的,具体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和孩子的数量。对于低收入家庭类型,尤其是子女较多的家庭,不领取福利对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实际收入偏差的影响比税收和SIC更显着。对于高收入家庭类型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换句话说,低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低于模拟,主要是因为他们收到的福利比模拟少,而高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家庭收入比模拟高,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和SIC比模拟少。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发现?在福利方面,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子女较多的家庭,更有可能表现出不领取福利的情况(见上文)。许多欧洲国家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Frericks 等人,2020 年;Saraceno,2006 年))。因此,如果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有资格获得更多福利,但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需要更频繁地申请,那么不接受的风险也会更高。由于这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实际福利与模拟福利之间的负偏差比其他家庭更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税收和SIC,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税率是成比例的,甚至常常是累进的(即高收入家庭缴纳的税款绝对金额高于低收入家庭)。如果我们假设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逃税和测量误差成比例相等,这导致高收入家庭的实际税收和模拟税收以及 SIC 之间的绝对偏差更大。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分析了实际和模拟税收以及 SIC 相对于家庭总收入的偏差(参见在线附录中的图 A1)。结果显示,七个国家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类型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最后,我们的税收和 SIC 结果显示,单身或夫妇家庭类型之间没有系统性差异。这意味着从整体情况来看——即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家庭总收入之间的差异——中高收入家庭类型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尽管如此,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低于模拟收入
如前所述,我们的研究采用探索性方法来分析基于国家的差异,因为不可能假设特定的国家集群。关于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类型的研究结果适用于所研究的七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然而,有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奥地利是一个特例,因为所有低收入和几乎所有中等收入家庭类型都缴纳比模拟更高的税收和SIC,而该国的福利负偏差最为明显。因此,对于奥地利低收入家庭来说,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七个国家的模拟收入。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奥地利,BMF,2022),中低收入家庭类型很可能经常不利用有利的法规。关于福利不领取的情况,很难对奥地利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评估,因为奥地利对福利不领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福利上(参见Fuchs 等,2020),被有意排除在本次分析之外。此外,荷兰的高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比模拟的要高得多。结合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中等负偏差,这反映了七个国家中家庭类型之间的最大差异(见表3))。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高收入家庭类型缴纳的税款和社会保障缴款比模拟的要少。我们观察到芬兰和斯洛文尼亚的 20 种家庭类型中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最小。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低收入不平等有关,在我们的样本中最低(2019年斯洛文尼亚的基尼系数为0.246,芬兰的基尼系数为0.273;经合组织,2022年),这可能会对人口遵循再分配政策的意愿产生积极影响法律规定的逻辑。
我们分析实际和模拟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偏差的方法决定强调了一个高度相关的再分配因素:确实有一些家庭(主要是高收入家庭类型)的收入更高。实际收入高于模拟收入。这种现象在现有的研究中已经使用术语“beta 错误”进行了讨论,这些错误呈现出一个残余类别,因为它们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行政决策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由于模拟错误(参见第 2 节)。我们的分析揭示了福利国家再分配中存在相当大程度的贝塔误差。这种现象仍然是再分配研究中一个相当隐蔽或被忽视的方面,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此外,尽管同事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将税收纳入再分配分析(Bradshaw 和 Nieuwenhuis,2021;Dingeldey,2001)),它们从未被系统地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对税收和 SIC 以及福利的分析为再分配提供了更多见解。税收和 SIC 方面的主要负偏差可能与 EUROMOD 执行的微观模拟的偏差有关。税收法规通常性质复杂,在 EUROMOD 中实施起来极具挑战性,因为可能会缺少导致税收减免的各种情况的具体信息。然而,即使我们假设存在这种偏差,其结果也有利于高收入家庭类型。
结论
再分配是当代社会秩序的关键要素之一,研究以多种方式对其进行了探讨。然而,它主要是在减贫和当前工作人口与非工作人口之间的再分配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家庭方面的社会再分配往往不被考虑,即使考虑到,也大多采用一维的家庭视角。此外,大多数研究在分析中对再分配和实际结果的规定是混合的。为了充分理解再分配,我们需要区分社会规范和正式商定的再分配与其他社会条件造成的实际结果。与再分配法规直接相关的结果甚至可能不足以得出我们关于再分配法规的结论,因为这些具体结果也可能偏离它们所依据的法规。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作为监管的再分配和再分配结果之间的对应程度。
衡量前者到后者的不平等转换向我们展示了再分配与官方商定的相符程度。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最终谁的境况实际上更好或更差。本文最初的方法论设置以实证的方式关注与家庭相关的再分配,使我们能够进行这项研究。我们通过确定家庭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并比较他们的实际和模拟净收入来调查这种差异。由于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家庭的总收入相同,因此该研究清楚地揭示了规定的再分配与实际结果的差异,而与影响总收入的各种因素无关。我们比较了20种家庭类型的偏差,我们根据收入水平区分了这些家庭类型,孩子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家长是单亲还是夫妇。此外,我们还比较了数据最好的七个欧洲国家: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芬兰、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为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研究了实际和模拟税收和 SIC 之间的偏差,以及作为可支配家庭收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和模拟福利之间的偏差。
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高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可支配家庭收入明显高于模拟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而低收入家庭类型则相反。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类型的实际收入与模拟收入之间的偏差最小。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七个国家;荷兰和奥地利最明显,芬兰和斯洛文尼亚最不明显。因此,监管再分配与实际再分配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类型缴纳的税款和社会保险费比模拟的要少,但获得的福利也较少。高收入家庭类型平均缴纳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明显低于模拟,但获得的福利略高于预期(特别是在芬兰、瑞典和拉脱维亚),或者与模拟福利的负偏差相对较低。对于低收入家庭类型,我们发现相比之下存在“累积劣势”,因为他们支付的税收和 SIC 仅比模拟低一点甚至更高(在少数情况下是奥地利和西班牙),而他们收到的福利金是明显低于模拟。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相关)往往会因法规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而加剧。瑞典和拉脱维亚)或仅表现出与模拟效益相对较低的负偏差。对于低收入家庭类型,我们发现相比之下存在“累积劣势”,因为他们支付的税收和 SIC 仅比模拟低一点甚至更高(在少数情况下是奥地利和西班牙),而他们收到的福利金是明显低于模拟。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相关)往往会因法规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而加剧。瑞典和拉脱维亚)或仅表现出与模拟效益相对较低的负偏差。对于低收入家庭类型,我们发现相比之下存在“累积劣势”,因为他们支付的税收和 SIC 仅比模拟低一点甚至更高(在少数情况下是奥地利和西班牙),而他们收到的福利金是明显低于模拟。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相关)往往会因法规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而加剧。他们收到的福利金明显低于模拟。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相关)往往会因法规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而加剧。他们收到的福利金明显低于模拟。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通常与再分配法规相关)往往会因法规转化为实际的再分配而加剧。
总结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福利国家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再分配法规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充分捕捉再分配的国际差异,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再分配的不平等。
最后,如何才能使不平等的转换变得更加平等?在税收方面,纳税申报往往依赖于对税收减免的深入了解,这对低收入家庭尤其具有挑战性,如上所示。相反,如果行政当局自动实行税收减免,更多的公民就可以从这些规定中受益。同样,就福利领取而言,复杂的规则和申请程序需要索赔人采取高度行动,往往与福利的歧视性或污名化性质相结合,导致相对较高的不领取率(见例如范·奥尔肖特,1998)。行政当局自动登记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家庭将增加福利的领取,特别是在经济状况调查福利的情况下。这可以改善许多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