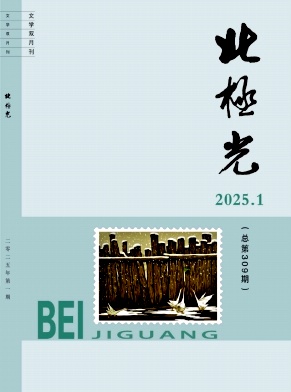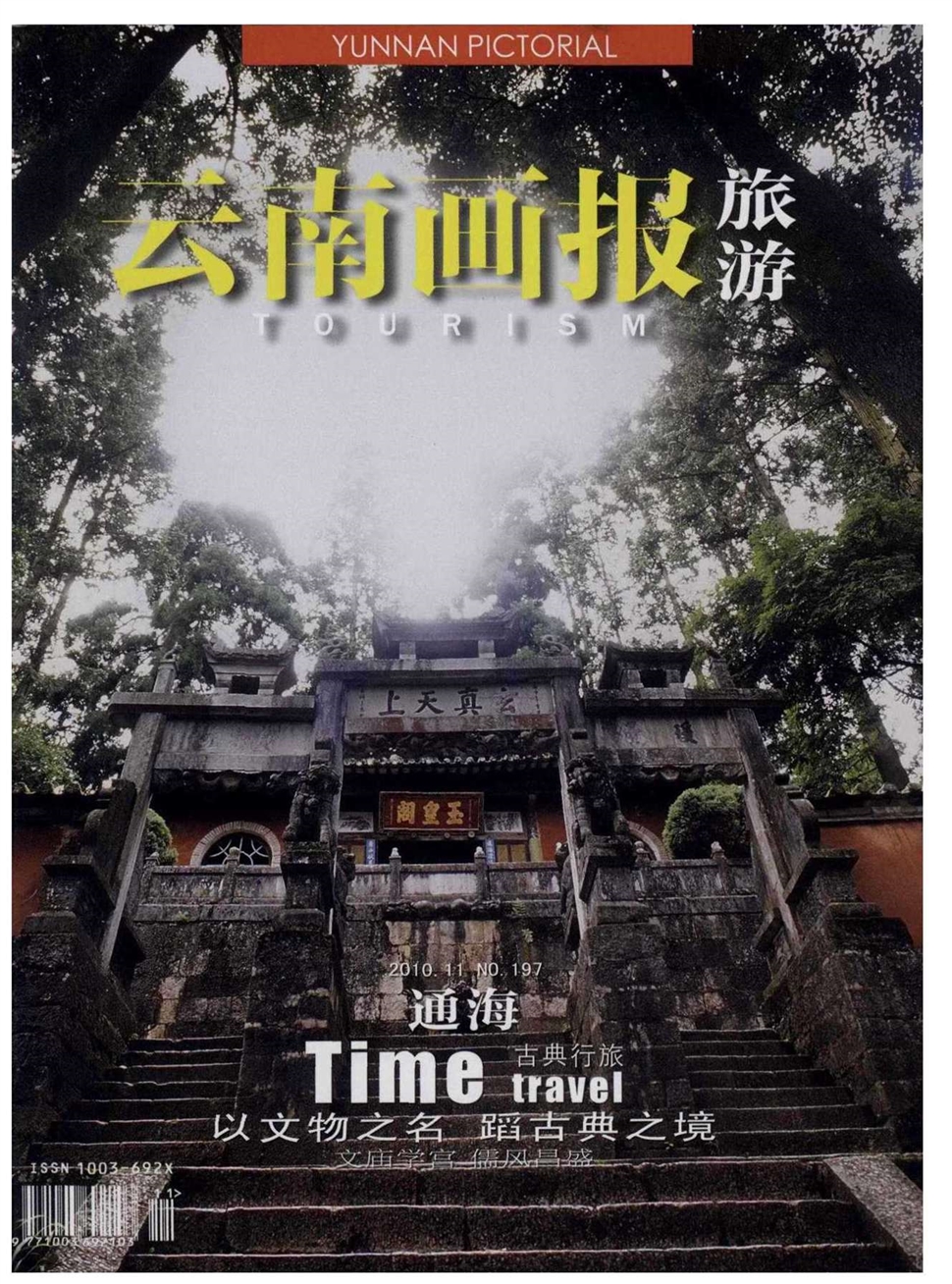新闻资讯
一、简介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同婚率(即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异性伴侣的百分比)有所上升(Katrňák 和 Manea)引文2020 年;诺姆和范·巴维尔引文2017年;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此外,在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夫妇中,一夫多妻制(他比她受教育程度高)减少,而低婚制(她比他受教育程度高)增加(Erát)引文2021 年;埃斯特夫等人。 引文2016)。脚注1然而,尽管的趋势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Domański 和 Przybysz)引文2007)。
理解为什么教育排序结果(例如同婚率、次婚率和一夫多妻率)会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结果表明了教育资源在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分配方式。由于教育是收入潜力的指标,妻子和丈夫教育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性别不平等,例如影响夫妻内部的性别分工(García Román引文2021)。此外,“谁嫁给谁”在教育方面可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不平等。例如,高比例的低学历和高学历同性伴侣可能表明夫妻之间存在高度的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Blossfeld 和 Timm)引文2003年;布林和安徒生引文2012年;施瓦茨引文2013)。
尽管教育分类结果对社会不平等具有潜在影响,但我们对为什么这些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的了解并不完整。研究通常不调查教育分类结果,而是应用对数线性模型来检查选型交配模式,即可用的女性和男性形成伴侣的非随机性程度(例如 Kalmijn引文1991年;施瓦茨和马雷引文2005年;斯密茨引文2003)。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揭示选型交配的趋势和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育分类结果,例如同配率。此外,对数线性模型控制结构性机会,即合作伙伴市场上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和男性的可用性。因此,结构性机会变化与教育排序结果之间的关系尚待研究。
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结构机会和教育分类结果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通常没有控制选型交配(Corti 和 Scherer)引文2021 年;埃拉特引文2021 年;埃斯特夫等人。 引文2016)。此外,Katrňák 和 Manea (引文2020)表明,观察到的教育排序结果趋势与丈夫和妻子随机匹配时出现的趋势相关。然而,据我们所知,只有两项研究试图阐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变化对教育分类结果趋势的单独影响(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这些研究发现,同婚和异婚的趋势主要与结构机会的变化有关。然而,现有的证据仍然支离破碎,因为以前的研究要么调查相对较短的时期,要么使用粗略的教育衡量标准(大学教育与非大学教育),要么只分析一个国家的教育排序趋势。此外,之前的研究并未考察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在解释教育分类结果的跨国差异方面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通过分析异性婚姻的教育分类结果(即同婚率、次婚率和多婚率)的跨国和跨时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结构性机会和差异的趋势和差异,从而解决了这些知识差距。选型交配。为此,我们使用分解方法,将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结果与假设的结果进行比较,假设另一年或国家的选型交配模式或结构机会已经到位(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
该分析利用了 2000 年至 2020 年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所有婚姻的独特人口数据。这些案例在理论上很有趣,因为由于高等教育扩张的开始和速度不同,它们的结构性机会存在很大差异。教育。此外,他们表现出经济和文化差异,并且属于不同的福利制度,这可能会影响伴侣的寻找行为。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做出了一些贡献。与大多数分析选型交配的研究相反,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婚姻中的教育分类结果。虽然一些研究探讨了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我们不仅研究趋势,还研究这些结果的跨国差异,以推进这一观点。此外,我们不是调查结合或婚姻的普遍程度(婚姻存量),而是调查婚姻的发生率(特定年份的契约婚姻)。这是一个更可取的措施,因为女性和男性的婚姻存量受教育程度可能会因教育升级以及分类离婚和死亡率而发生变化。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考察了自 1999 年博洛尼亚进程启动以来过去 20 年婚姻教育排序的趋势,并用有关选型交配和教育排序结果的最新趋势的证据更新了文献。
2 理论背景
2.1. 合作伙伴搜索框架
合作伙伴搜索理论(英格兰和法卡斯引文1986年;奥本海默引文1988)假设伴侣搜索过程的结果取决于三个因素:女性和男性对具有特定特征的候选人的偏好、伴侣市场上首选候选人的可用性以及伴侣搜索行为。首选候选人的宏观结构可用性和合作伙伴搜索行为会影响“谁遇见谁”。例如,延长合作伙伴搜索的持续时间可以增加遇到首选候选人的机会。此外,首选候选人在空间(例如地区或社区)和社会环境(例如工作场所或体育俱乐部)的分布也可能会影响会面机会(Feld引文1981年;范·巴维尔引文2021)。此外,由于工会的形成不是个人的决定,而是需要双方同意的共同决定,女性和男性的偏好以及双方的匹配机制影响着寻找伴侣过程最后阶段的教育排序结果(Van Bavel)引文2021)。
该框架的几个概念,例如合作伙伴偏好或搜索行为,已被证明难以衡量,因为数据通常只能从现有工会获得。因此,大量研究研究了教育选型交配的变化,即教育分类结果的非随机性程度。由于这些研究仅控制宏观层面上的结构机会,因此伴侣搜索过程中的所有其他机制(例如伴侣偏好、候选人的空间分布和两侧匹配)都会形成选型交配模式。为了与该框架进行比较,我们讨论了为什么结构性机会和选型交配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教育分类结果。
2.2. 结构性机会
根据布劳的结构理论,人口中某个群体的相对规模决定了遇到该群体成员的概率(布劳)引文1977 年;布劳等人。 引文1982)。这意味着与具有特定教育水平的人见面并结婚的可能性取决于该教育群体在人口中的相对规模。例如,如果很少有人受过高等教育,那么遇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与之结婚的概率就会很低。
近几十年来,由于高等教育的全球扩张,合作伙伴市场上教育集团的相对规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Schofer 和 Meyer引文2005)。布劳的结构理论表明,当合作伙伴市场上存在大量受过同等教育的候选人时,受过同等教育的个人之间匹配的机会就很高。这种情况发生在教育扩张过程的早期和晚期,此时大多数人要么受教育程度低,要么受教育程度高(Katrňák 和 Manea)引文2020 年;米基耶吕特引文1972)。
尽管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张,但这一过程的起点和速度各不相同(OECD引文2022b)。因此,在某一年,不同国家/地区的合作伙伴市场构成不同。我们预计,在合作伙伴市场中受过同等教育的候选人比例较高的国家,同婚率会更高。总之,在分析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时,我们预计合作伙伴市场上受过同等教育的候选人的比例与同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此外,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即教育水平内的男女比例,也影响着结构性机会。一般来说,我们预计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的相似性越高,结识和结婚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候选人的机会就越高。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近几十年来出现了逆转(De Hauw等,2017)。 引文2017年;迪普雷特和布赫曼引文2013年;埃斯特夫等人。 引文2016)。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改善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之间的结构性会面机会。脚注2此外,各国教育性别差距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的教育排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时,我们假设高等教育中对女性有利的性别差距与较高的低婚率和较低的一夫多妻率相关。
总而言之,我们不仅期望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候选人的比例与同婚率之间存在关系,而且还期望女性的教育优势与低婚率和多婚率之间存在联系。然而,教育扩张的趋势和差异以及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或加强,因为它们在经验上是一致的。
2.3. 选型交配
许多研究表明,根据各种社会人口和社会文化特征(包括教育程度)进行的婚姻排序具有非随机性(Kalmijn引文1991年,引文1998年;施瓦茨和马雷引文2005年;斯密茨等人。 引文2000)。我们简要讨论了四种机制,可以解释本世纪头二十年选型交配的趋势和国家差异。
首先,在线约会的日益普及(Potarca引文2020 年;罗森菲尔德等人。 引文2019年;罗森菲尔德和托马斯引文2012)改变了女性和男性相遇的社会环境。在线约会提供了多样化的环境,结识不同教育水平的候选人的机会很高。然而,它也降低了搜索成本,并提供了有关合作伙伴市场上可用候选人的信息,这可能有助于同质率的上升(Schwartz)引文2013)。现有证据表明,尽管在线约会不会随机产生情侣,但与传统的伴侣搜索模式相比,它往往会充当社交混合体,导致情侣分类更加多样化(Potarca)引文2017年,引文2020 年;托马斯引文2020)。
其次,性别平等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可能导致伴侣偏好趋同,因为男性开始受益于拥有受过高等教育、收入前景更高的伴侣(Mare)。引文1991)。尽管女性继续从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伴侣中受益,但她们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能够根据与经济成功无关的理想特征来选择伴侣(Han引文2022 年;奥本海默引文1994年;施瓦茨引文2013)。这可能导致一夫多妻制的减少以及同婚和低婚制的增加。
第三,教育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可能会影响选型择偶,因为它们表明某人在与教育水平“低下”的人结婚时可能会损失多少(Fernandez等,2017)。 引文2005年;施瓦茨引文2013)。当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结婚成本较低时,同质婚姻可能会变得更有可能,因为个人在选择伴侣时可能会优先考虑教育程度而不是其他属性。
第四,福利制度可能影响选型交配(Domański 和 Przybysz引文2007)。在瑞典等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慷慨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使福利与市场和家庭脱钩(Esping-Andersen引文1999)。在这种情况下,地位的获得对于选择伴侣来说可能不那么重要,从而可能削弱丈夫和妻子教育之间的联系。意大利作为地中海福利国家,具有双重保护制度和有限的支持母亲就业的政策(例如幼儿的公共托儿服务)(Del Boca 和 Vuri)引文2007年;纳尔迪尼和萨拉切诺引文2008)。因此,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比女性更重要。与其他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类似,捷克共和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经历了福利紧缩和重新家庭化的过程(例如通过减少公共儿童保育支出)(Saxonberg 和 Sirovátka引文2009年;萨克森伯格和塞莱瓦引文2007)。福利的缩减表明,女性和男性的社会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伴侣的寻找过程,而重新家庭化可能表明男性的资源比女性的资源更重要。
总而言之,选型交配是由多种共同运作的伙伴搜索和选择机制形成的。上面的理论论证让我们期望观察到(a)国家内部选型交配随时间的变化和(b)国家之间选型交配模式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调查了国家内部趋势和国家间差异在选型交配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分类结果趋势和差异的结构机会。
2.4. 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的结构性机会和选型交配
在本世纪的头 20 年里,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合作伙伴市场的结构性机会。脚注3高等教育的早期扩张是瑞典的特点。2000年,25至34岁人群中已有33.6%接受了高等教育。在随后的 20 年里,高等教育继续增长,达到 49.1%,这表明接受最高教育水平的个人越来越集中(OECD引文2022b)。在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2000年25岁至34岁男性和女性的总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捷克共和国,高等教育从2000年的11.2%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33.0%,在意大利,高等教育从 2000 年的 10.4% 增长到 2020 年的 28.9%(经合组织)引文2022b)。在这三个国家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上升速度快于男性,从而扭转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De Hauw等,2017)。 引文2017)。
此外,这三个国家的合作伙伴选择和匹配机制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国家代表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福利背景。在瑞典,有几个因素表明,同婚的可能性比其他欧洲社会要小。瑞典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促进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经合组织)引文2022a)。此外,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经合组织引文2020),并且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可能使异性恋匹配更有可能(Domański 和 Przybysz引文2007年;英格尔哈特引文1999)。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期望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意大利,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经合组织引文2020)为同质匹配提供激励。然而,家庭提供的福利和照顾以及女性就业率低至 50% 左右(OECD引文2022a ) 可能会促进一夫多妻制匹配。在捷克共和国,女性就业率很高(OECD引文2022a),尽管儿童保育的公共支出有所减少。此外,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经合组织引文2020),尽管教育回报往往很高(黑山和帕特里诺斯)引文2014),这可能会影响与“下层”结婚的教育成本。
根据经验,瑞典的选型交配率明显低于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Domański 和 Przybysz引文2007年;卡特里克和马内亚引文2020)。然而,只有少数研究调查了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的教育选型交配趋势。现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选型交配减少,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丈夫和妻子的选型交配增加(Katrňák 和 Manea)引文2020)。最终,结构性机会和选型交配会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它们都会影响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
3. 方法
3.1. 数据
我们的数据包含 2000 年至 2020 年(2000 年、2002 年、……、2020 年)偶数年间在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缔结的所有婚姻的信息。脚注4这包括第一次婚姻和更高次婚姻。附录中的表 A1 显示了按年份和国家划分的缔约婚姻的绝对数量。我们总共分析了 3,285,848 桩婚姻。
这些数据提供了婚姻发生率的精确衡量标准。与之前许多研究的普遍性指标(婚姻存量)不同,发生率指标(新成立的婚姻)不受婚后变化的影响,例如教育程度的提高或选型离婚。因此,发生率测量有利于研究婚姻排序的变化。此外,这些数据不会受到抽样偏差的影响,因为它们包含所有契约婚姻的信息。
然而,跨国差异和未婚同居发生率的变化可能会质疑仅关注已婚夫妇的适当性(Kiernan引文2001年;普里乌引文2006)。例如,在瑞典,同居现象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普遍(Kiernan引文2001)。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往往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和男性更频繁地同居(Bumpass 和 Lu引文2000;施瓦茨引文2010)。同居婚姻的教育选择性的趋势和跨国差异可能会通过塑造已婚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构成来影响我们的结果。例如,如果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越来越多地选择同居而不是结婚,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最终结婚的人的一夫多妻率下降。研究还表明,同居者和已婚夫妇之间的选型交配模式有所不同(Blackwell 和 Lichter)引文2000;埃斯特夫等人。 引文2013年;舍恩和韦尼克引文1993)。如果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或因国家而异,它们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然而,从经验来看,这些机制对婚姻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存在这种潜在的局限性,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婚姻,因为同居婚姻的可靠发生率衡量标准并不容易获得,而婚姻发生率是由国家统计局明确定义和记录的。
在所有分析的国家中,2020 年订婚数量均大幅下降,这很可能与 COVID-19 大流行早期阶段对婚礼施加的限制有关,例如限制宾客人数。2018年至2020年,意大利的契约婚姻数量减少了一半,捷克共和国和瑞典的契约婚姻数量下降了20%以上。此外,2008年,捷克共和国引入了不识别丈夫和妻子教育程度的选择。由于这种做法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因此我们样本中的契约婚姻数量有所下降。在解释结果时,需要考虑这一点,因为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个人是否报告其教育水平。
3.2. 测量
教育排序结果。为了衡量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的共同分布,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低、中低、中、高和高。虽然这些水平在不同国家的受教育年限方面并不具有严格可比性,但它们确实反映了各国统计局制定的教育系统中特定国家的有意义的差异。在附录中,我们提供了有关该措施可比性的详细信息。此外,附录中的表B1至B3显示了所有婚姻表(描述丈夫和妻子教育程度的列联表)。为了实现一种可以直观解释的教育分类结果衡量标准,我们将这些结果分为三类,以区分同质性(妻子和丈夫受教育程度相同)、
结构性机会。我们利用在特定年份和国家结婚的丈夫和妻子的教育构成来衡量结构性机会。因此,在婚姻表中,边际分布反映了结构性机会。这种结构性机会的近似有两个局限性。首先,不结婚的人可能已经出现在伴侣市场上。因此,婚姻中的教育梯度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Bertrand等人,2014)。 引文2021 年;卡尔迈因引文2013)可以影响结构性机会的衡量。例如,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表明,在爱尔兰,教育排序结果趋势的一小部分但不可忽视的部分与工会形成中教育梯度的变化有关。其次,我们观察同一时期内不同群体的婚姻情况。因此,女性和男性的结婚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经合组织引文2019 ) – 影响在特定年份结婚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对某一时期结构性机会的衡量包括可能属于不同合作伙伴市场的不同出生群体的个人。然而,通过用边际分布衡量结构机会,我们实现了与控制边际分布来研究选型交配的大量研究的可比性(例如马引文1991年;施瓦茨和马雷引文2005)。
选型交配。与之前的文献一致,我们采用婚姻表中的优势比结构来衡量选型交配。婚姻表中的优势比反映了丈夫和妻子的教育净结构性机会之间的关联。
3.3. 分析方法
我们的分析涉及四个步骤。首先,我们研究了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的绝对同质性、低配性和多配性率的趋势。其次,我们通过分析妻子和丈夫受教育程度的趋势来调查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在第三步中,我们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选型交配进行建模。最后,我们分析了教育排序结果的国内趋势和国家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趋势和差异。为此,我们应用了 Leesch 和 Skopek 引入的分解方法(引文2023)。使用 LEM 软件(Vermunt引文1997),而 Stata 16 用于其余分析。
分解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我们交换两个婚姻表之间的比值比或边际分布,并确定与比值比和边际分布的反事实组合相匹配的单元格频率。表格1表明有两个观察到的或实际的婚姻表和两个假设或反事实的婚姻表。在每个表中,我们计算了所需的教育排序结果,例如同质结合的比例。Y
表示观察到的或事实的排序结果,并且Y˙
代表假设或反事实的排序结果。当然,排序结果来自于观察到的表格1(例如,在县 1 或时间 1 观察到)的优势比和边际分布为表格1 (Y11)
。结果在表2通过比值比和边际分布获得表2 (Y22)
。反事实的婚姻排序结果反映了以下的优势比:表格1和边际分布表2(Y˙21
) 或优势比表2和边际分布表格1(Y˙12
)。
在交换优势比或边际分布后,我们通过使用迭代比例拟合(IPF)(Deming 和 Stephan)获得了反事实婚姻表引文1940年;洛马克斯和诺曼引文2016)。IPF 将一个表中的单元格交替调整为另一个表的行和列总计,而不改变初始表的优势比结构。将单元格重新缩放为行和列总计的过程继续迭代,直到所有单元格都匹配预定义的优势比结构和边缘分布,从而产生所需的反事实表。
第二步,我们使用反事实和观察到的婚姻表来分析教育排序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差异。为了调查教育排序中趋势和国家差异的结构性机会的作用,我们在比值比固定为后比较了两个表之间的教育排序结果(例如同配率)。表格1 (Y˙21−Y11)
并在表2 (Y22−Y˙12)
。在这两次比较中,教育排序结果仅在边际分布上有所不同。我们根据两个边际分布分量计算了平均边际分布分量。相应地,平均比值比分量是在边际分布固定为后从教育排序的差异中获得的表格1(Y˙12−Y11
) 和表2(Y22−Y˙21
)。附录中提供了该方法的正式阐述。
该方法仅允许成对比较。因此,为了分析各国婚姻教育程度排序的趋势,我们将每年的婚姻表与2000年的结婚表进行了比较(每个国家内进行10次比较)。为了分解跨国差异,我们比较了两国同一年内的结婚表(11个时间点各比较3次)。复制文件可通过https://doi.org/10.17605/OSF.IO/AYGH5在开放科学框架中获取。
4. 结果
4.1. 婚姻中的教育排序结果
图1显示了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婚姻中的教育排序结果。实线描绘了观察到的教育排序结果。虚线将在下一节的末尾讨论,因为它们反映了结构性机会。每年,在这三个国家,大多数婚姻都是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缔结的,低婚率(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高于一夫多妻率(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然而,不同国家的教育排序结果差异很大。截至 2018 年,同婚率在瑞典最低,在意大利最高。低婚率和一夫多妻率在瑞典最高,在意大利最低,捷克共和国介于两者之间。
从2000年到2020年,教育排序结果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瑞典,同婚率上升,一夫多妻率下降,低婚率维持在32%左右的稳定水平。在捷克共和国,同婚率在 54.5% 至 59.7% 之间波动。低婚率有所增加,一夫多妻率从2000年的19.6%下降到2014年的14%左右,此后几乎没有变化。在意大利,同婚率截至 2018 年有所增加,但去年大幅下降。低婚率没有明显的趋势,截至 2018 年,一夫多妻率有所下降,随后在 2020 年大幅上升。
2020 年意大利教育排序结果的显着变化可能与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有关。意大利是第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欧洲国家,并实施了一些欧盟最严格的封锁措施(Plümper 和 Neumayer)引文2022)。社交距离措施禁止在 2020 年春季举行婚礼,后来又转为严格限制宾客人数。需要进一步研究来了解 2020 年意大利教育分类结果的深刻变化。第一个证据表明,COVID-19 大流行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结婚意向(Guetto 等人,2019)。 引文2021)。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夫妻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取决于双方的教育程度,例如,大流行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是否与就业不确定性有关。
4.2. 结构性机会
图2显示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的趋势。在所有国家,高等教育都大幅扩展。捷克共和国的高等教育增长迅速,尤其是妻子的高等教育,从 2000 年的约 10% 增长到 2020 年的 40.4%。在瑞典和意大利,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稍慢。在瑞典,高等教育在2000年就已普及(妻子为40.4%,丈夫为35.7%),而在意大利,只有少数人(约10%)受过高等教育。在所有国家,丈夫的高中教育程度都有所提高,但妻子的教育程度保持稳定或下降。各国丈夫和妻子的中低文化程度均显着下降,低文化程度的人在所有年份和国家中构成了最小的群体。
尽管这三个国家的教育程度的主要趋势相似,但它们不一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结构性机会的趋势。在低教育背景下,教育扩张通常会导致教育水平的更大差异。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教育扩张与个人日益集中于少数教育水平有关。为了证明这一点,差异指数图2显示需要重新分配以实现每个教育类别均占同等份额的分配的案例比例。脚注5在瑞典,丈夫和妻子的差异指数有所上升。这意味着教育水平的差异有所下降。对于意大利丈夫和妻子来说,该指数从2000年到2018年一直在下降,而在捷克共和国,该指数在2008年之前一直下降,之后又有所上升。因此,各国教育差异的趋势存在很大差异。
此外,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在瑞典,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与丈夫的比例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了逆转。在意大利,这一比例在2002年和捷克共和国在2008年发生了逆转。近年来,所有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与丈夫的比例达到了约1.3 。为了说明这一点,附录中的图 A1 绘制了教育特定性别比例的趋势。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结构性机会的趋势,图中的虚线图1显示丈夫和妻子随机匹配时的教育排序结果,并且教育排序结果仅由结构机会决定。脚注6观察到的和结构性的教育排序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没有选型交配,同配率会较低,异配率会较高。此外,如果匹配完全随机,那么教育排序结果的国家差异将会更小。这表明选型交配会导致国家间分类结果的差异。此外,如果没有选型交配,分类结果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瑞典,同质婚姻会增加,而一夫多妻制会减少。这表明结构性机会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相关。
4.3. 选型交配
为了研究选型交配的趋势和国家差异,我们估计了对数线性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交互参数是优势比。该模型控制了结构性机会,因为优势比对于总样本量以及行和列边际分布的变化是不变的(Agresti引文2002年;鲍尔斯和谢引文2008年;冯·埃和蒙引文2013)。脚注7
我们提供了所有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数据表2。模型1是零关联模型,假设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MW)之间不存在关联。该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效果非常差 – 它的 BIC 为正(Raftery引文1995),错误分类了超过 25% 的婚姻,L 2为 65,483,自由度为 297。模型 2 是恒定关联模型,假设丈夫和妻子的教育 (MW) 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时间和国家中是恒定的。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明显好于零关联模型,但仍然较差,这表明选型交配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BIC 标准仍然为正)。
模型 3 基于模型 2,但包含 32 个附加参数,用于确定每个国家丈夫和妻子教育 (MW) 之间关联的趋势。它是均匀差异模型(Erikson 和 Goldthorpe引文1992)或对数乘法模型(Xie引文1992)假设关联模式(MW)在不同国家和时期以相同的方式变化。在该模型中,L 2显着下降(与模型2相比下降77%;与模型1相比下降97%),相异指数下降,BIC变为负值。然而,L 2 /df 比率表明这不是解释我们的数据的最令人满意的模型(L 2 /df = 6.62)。模型 4 与模型 3 相同,但我们“屏蔽”了表格中的主对角线,因为它是从社会分层研究中得知的(Breen 和 Luijkx引文2004年;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引文1992年;豪瑟引文1978)表明关联主要集中在对角线上。这种“遗传效应”通常会覆盖数据中的任何其他模式。因此,我们在所有表中包含了对角单元格的 128 个参数(33 个分析表乘以对角线上的 4 个单元格,减去属于基本关联的 4 个单元格)。模型 4 比之前的模型更适合数据(L 2 /df = 2.61,Δ = 0.82%),但 BIC 标准高于模型 3,表明模型高估(识别了超出必要的参数)。
为了放宽均匀差异的假设,我们计算了回归型层效应模型(参见 Goodman 和 Hout引文1998年,引文2001)。模型 5 假设国家和时期之间的关联模式 (MW) 呈线性但非均匀变化(有关将此模型扩展到四向数据的信息,请参阅 Katrňák 和 Manea引文2020)。根据 BIC 的说法,模型 5 比模型 3 和 4 更简洁,并且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更好。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分再现数据(L 2 /df = 4.07;Δ = 2.38%)。因此,在模型 6 中,MW 关联的变化被建模为随时间变化的分类模型,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呈线性变化。模型 7 的假设相反:MW 关联的变化随时间呈线性变化,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呈线性变化。最后,模型 8 假设 MW 关联的变化是跨时间和国家的分类。模型 7 最适合数据(BIC = −2338;L 2/df = 2.73; Δ = 1.95%)。MW 模式的变化被建模为线性模型,由一个参数表示,但作为跨国家的分类模型,由每个国家的一个参数表示。根据模型7,我们得出结论,所有国家都存在选型交配,但不同国家选型交配的强度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型交配的趋势相对呈线性。
图3呈现每个婚姻表单元格选型交配的趋势和跨国差异。的行图3显示男性的教育水平(L - 低,LI - 中低,UI - 中上,H - 高)。在专栏中,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教育水平。在每个方块内,我们描绘了每个时期和国家的 Model 7 的参数。X 轴显示年份的模型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年份不按时间顺序排列,以便于对 MW 关联中的线性变化和距离进行建模。高于 0(虚线)的参数表明,与所有国家和时期的平均选型交配相比,这种教育组合的机会更高。如果它们低于 0,则与平均选型交配相比,教育组合的机会较低。
在所有国家,同质配种交配(对角线)图3) 在教育分布的边缘(低教育和高等教育)较高。此外,配偶教育水平之间的较大差异与教育组合发生的机会较低相关。在瑞典,同质选型交配在所有教育类别中是最低的。此外,该模型表明所有国家的趋势相似,并且在整个分析期间变化相对较小。在除高等教育之外的所有教育类别中,同质选型交配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年份在 X 轴上并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从左到右排序的。从第一年组(2000-2004年)、第二年组(2006-2012年)到第三年组(2014-2018年),前三个教育类别的同配选型交配有所增加。2020 年标志着这一趋势的变化,表明选型交配有所减少。除了高等教育之外,所有教育类别中的异性配型交配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观察到机会结构和选型交配的跨国和跨时间变化。在下一节中,我们分析了在婚姻中观察到的教育排序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结构性机会和选型交配来解释。
4.4. 婚姻中教育排序结果的分解
图4呈现了婚姻中教育排序结果趋势的分解结果。浅灰色和深灰色条的总和等于与 2000 年参考年相比观察到的同质性、低配性和多配性率的差异。浅灰色条显示教育排序结果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选型交配的趋势。深灰色条表示改变机会结构对教育排序结果趋势的重要性。准确的分解结果和标准误差如附录中的表A2至A4所示。标准误差是通过对 500 个样本进行放回重新采样来估计的。此外,附录中的图 A2 描述了仅选型交配(绿线)或结构机会(红线)发生变化时教育排序的趋势。
同质婚姻的趋势。不同国家的同配率上升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性机会的趋势是不同的。在瑞典,不断变化的机会结构和选型交配模式都导致同配率上升。例如,从2000年到2020年,同质婚姻率增加了6.4个百分点。选型交配的变化占这一趋势的3.2个百分点,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占3.2个百分点。在捷克共和国,同婚率波动,没有明显的趋势。这种模式几乎完全归因于选型交配的趋势。在意大利,2004年至2018年同质婚姻的增长完全是由选型交配的变化推动的。如果只改变结构性机会,同性婚姻的比例就会下降。因此,如果结构性机会没有改变,同性婚姻比例的上升会更加明显。此外,2020 年同配性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选型交配的变化。
低配现象的趋势。在瑞典,自世纪之交以来,低配婚姻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我们的分解分析表明,这种明显的稳定性是由两个相反力的平衡造成的。如果 2000 年和 2020 年之间只有选型交配有所不同,我们就会观察到低配率下降 1.6 个百分点。然而,如果2000年和2020年仅在结构性机会上有所不同,低婚率将会增加1.3个百分点。在捷克共和国,结构性机会的变化是低婚现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意大利,结构性机会的趋势与低婚率的上升有关,而选型交配的趋势则与低婚率的下降有关。就像在瑞典一样,这两种趋势主要是相互抵消的。
一夫多妻制的趋势。总体而言,一夫多妻制在这三个国家都在下降。尽管一夫多妻制的趋势相似,但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因国家而异。在瑞典和捷克共和国,一夫多妻制的减少主要归因于结构性机会的变化。例如,在瑞典,一夫多妻制从 2000 年到 2020 年下降了 6.0 个百分点;这一下降的 4.5 个百分点归因于机会结构的变化。相比之下,在意大利,截至 2018 年,选型交配趋势是导致一夫多妻制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结构性机会的趋势与低婚率上升和一夫多妻率下降之间存在关联。
总之,尽管教育分类结果的趋势相似,但这些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结构性机会和选型交配的趋势,各国之间存在差异。然而,我们发现结构性机会的趋势与低配率的上升和多配率的下降有关,而选型交配的趋势往往与同配率的上升有关。
图5显示了教育排序结果中国家差异的分解。附录中的表 A5 至 A7 提供了精确值和标准误差。浅灰色和深灰色条的总和等于指定年份观察到的同质性、低配性或多配性率的差异。例如,图 (a) 中的第一个条显示 2000 年意大利的同婚率比瑞典高 18.8 个百分点。浅灰色条表明这种差距可以归因于选型交配的差异。深灰色条表明,如果意大利和瑞典之间的结构性机会没有差异,同婚率的差距甚至会略高。总体而言,观察到的国家教育排序结果之间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国家间选型交配的差异。
同质婚姻的国家差异。2000年至2018年,同婚率最高的是意大利,最低的是瑞典。这些差异几乎完全与选型交配的差异有关。捷克共和国和瑞典之间同配率的差距主要归因于选型交配的差异。负的深灰色条表明,如果结构机会没有差异,观察到的同质性差异甚至会更加明显。此外,在整个观察期间,选型交配成分大幅下降,表明选型交配模式的趋同有助于同配率的趋同。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同配率差异是由选型交配和结构性机会驱动的。然而,结构性机会的组成部分是:
低婚制的国家差异。低婚率在瑞典最高,在意大利最低。低配率的国家差异主要与不同的选型交配模式有关。例如,2018年,意大利的低婚率比瑞典低12.2个百分点。其中 9.5 个百分点可归因于选型交配,2.7 个百分点可归因于结构机会。然而,由于捷克共和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选型交配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差异。瑞典的一夫多妻率普遍最高,其次是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这些模式主要归因于选型交配的差异。在大多数年份,结构性机会的差异会产生抵消“效应”。这意味着,如果结构性机会相同,一夫多妻制的差距将会更加明显。这种模式的唯一例外是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国之间的一夫多妻率差异,这部分源于结构性机会的差异。
总之,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分类结果的跨国差异主要归因于选型交配的差异。相比之下,国内结构性机会的趋势对于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更为重要,尤其是低婚率和多婚率的趋势。
5. 讨论
我们的研究利用 2000 年至 2020 年间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水平婚姻发生率数据,试图解释教育排序结果的国内趋势和跨国差异。首先,我们研究了结构性机会、选型交配和教育分类结果如何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随后,我们分析了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结果的趋势和差异。
就国内趋势而言,我们发现同质婚姻(妻子和丈夫受教育程度相同)和次婚婚姻(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比例要么增加,要么保持稳定。在这三个国家,一夫多妻制婚姻(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的比例均下降。使用对数线性模型,我们发现同配选型交配略有增加,而异配选型交配的变化很小。分解结果表明,瑞典和意大利的选型交配趋势有利于同性婚姻,不利于异性婚姻,而捷克共和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此外,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导致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在这三个国家中,我们认为这些变化是低婚率上升和一夫多妻率下降的驱动力。结构性机会变化对同婚婚姻比例趋势的影响因国家而异。此外,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结果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变化,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尽管选型择偶和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始终与一夫多妻制婚姻比例的下降有关,但在瑞典,“结构性机会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在意大利,“选型择偶效应”则更强。结构性机会变化对同婚婚姻比例趋势的影响因国家而异。此外,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结果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变化,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尽管选型择偶和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始终与一夫多妻制婚姻比例的下降有关,但在瑞典,“结构性机会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在意大利,“选型择偶效应”则更强。结构性机会变化对同婚婚姻比例趋势的影响因国家而异。此外,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结果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的变化,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尽管选型择偶和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始终与一夫多妻制婚姻比例的下降有关,但在瑞典,“结构性机会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在意大利,“选型择偶效应”则更强。
对于跨国差异,我们发现意大利的同婚婚姻比例最高,其次是捷克共和国和瑞典,比例较低。相反,瑞典的低婚率和一夫多妻率最高,而意大利则最低。通过对数线性分析,我们发现同性配种和异性配种交配方面存在显着的跨国差异。分解结果表明,选型交配的这些差异对于塑造各国教育分类结果的差异至关重要。因此,尽管实际教育分布存在差异,但结构性机会的跨国差异在解释各国同婚和异婚结果差异方面的相关性较小。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了解国内教育排序结果趋势的结构性原因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例如,研究人员假设,女性相对于男性社会经济成就的提高可能导致低配性的增加和重配型选型交配的减少(Han引文2022 年;施瓦茨引文2013)。另一项研究认为,高等教育中性别差距的逆转改变了结构性机会,导致低婚率和高婚率婚姻和婚姻的增加(De Hauw等人,2017)。 引文2017年;埃斯特夫等人。 引文2016年;范·巴维尔引文2012)。我们的研究可以为这场辩论做出贡献。根据结构性解释,我们发现,仅结构性机会的变化就会导致从一夫多妻制婚姻向一夫多妻制婚姻的转变。然而,如果仅改变选型交配,次婚制和重婚制婚姻的比例都会下降。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提高而导致的选型择偶模式的改变,并不是女性在教育领域“下嫁”的“非传统”婚姻激增的主要驱动力。
这项研究的结果还提高了我们对各国教育排序结果差异的理解。学者们预计,经济不平等或福利制度等因素会影响选型交配的跨国差异(Domański 和 Przybysz)引文2007年;费尔南德斯等人。 引文2005年)。虽然我们的研究无法调查为什么选型交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这些差异在解释国家之间同质性和异质性结果差异方面的作用。这强调了研究跨国选型交配差异背后的原因的重要性。此外,尽管各国丈夫和妻子的教育构成存在差异,但结构性机会的跨国差异对教育排序结果的影响很小。这表明同婚、次婚和重婚婚姻群体的教育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尽管瑞典和意大利如果仅在结构性机会上有所不同,那么它们的同婚率也会相似,与意大利相比,瑞典受过高等教育的同婚婚姻可能更多。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教育分类结果的跨国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按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即婚姻表中的每个单元格)分类的这些结果。脚注8
我们的研究推进了现有的研究,探索改变结构机会和选型交配模式在塑造教育分类结果趋势中的作用。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之前的发现,将结构性机会的变化与低婚制的增加和一夫多妻制的减少联系起来(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然而,与之前的研究(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我们发现选型交配的变化是同配性增加的重要驱动力。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与我们的研究相比,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研究了不同的国家背景(爱尔兰)和时间范围(1991-2016),并使用婚姻存量数据而不是发病率数据。此外,现有文献使用了不同的教育程度衡量标准,并重点关注年轻的有伴侣女性,而我们则纳入了所有婚姻(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因此,工会形成时间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这些结果的差异。
最后,我们注意到我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首先,从概念上讲,我们将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视为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如果结构机会塑造了选型交配,则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反之亦然。例如,想要寻找受过高等教育的伴侣的个人可能会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这是我们的研究与该研究领域的其他分解分析(例如 Leesch 和 Skopek引文2023;佩尔曼耶等人。 引文2019)以及选型交配研究中对数线性建模的悠久传统(例如 Kalmijn引文1991年;马雷引文1991年;施瓦茨和马雷引文2005)。
其次,婚姻选择的变化和跨国差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结果。里施和斯科佩克(引文2023)发现爱尔兰工会形成的教育梯度变化与教育排序结果之间存在微小但不可忽视的联系。近几十年来,瑞典、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的婚姻教育梯度保持相对稳定,但各国之间差异很大(Bertrand等,2017)。 引文2021)。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与国内趋势相比,针对教育的工会选择可能对教育排序结果的跨国差异产生更显着的影响。
第三,研究表明,已婚夫妇和未婚同居者之间的选型交配有所不同(Blackwell 和 Lichter)引文2000;舍恩和韦尼克引文1993)。如果这些差异随着时间或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教育排序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的发现。此外,由于我们的数据包括第一次婚姻和更高次婚姻,因此再婚选择性的差异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结果。
第四,选型交配模式和教育分类结果可能对所选教育类别敏感(Gihleb 和 Lang引文2016),这通常是选型交配和教育分类结果研究的局限性。在本研究中,教育分类在各国之间并不严格具有可比性,而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的教育系统边界。因此,特别是在比较各国的教育排序结果时,教育的衡量可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限制。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实证了解同质婚姻和异质婚姻结果的趋势和跨国差异。这是第一项将跨国教育分类结果差异主要与选型交配差异联系起来的研究。此外,我们还为一小部分但不断增长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些研究分析区分了选型交配和结构机会对教育分类结果趋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