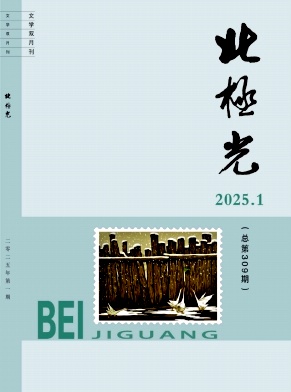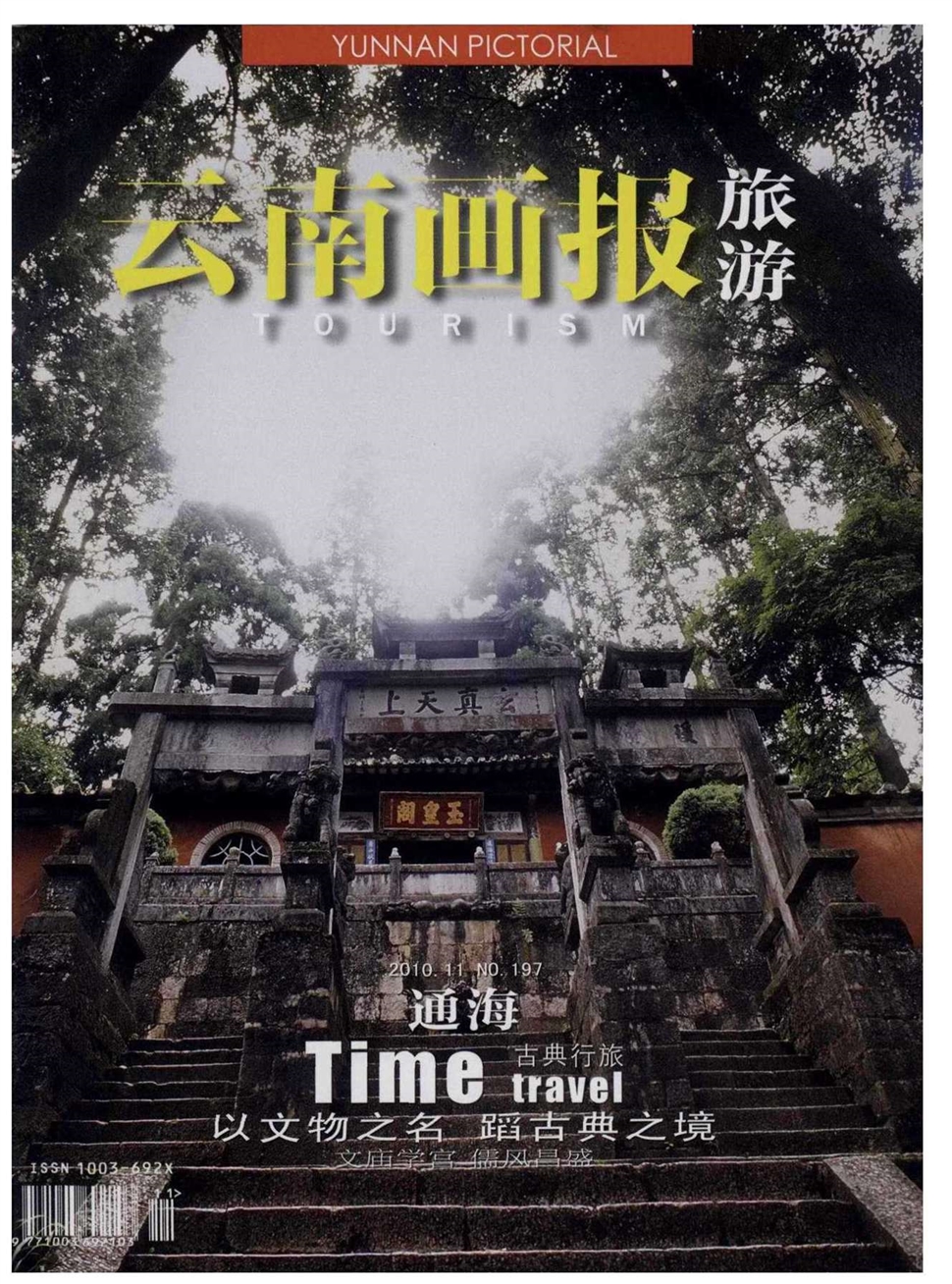新闻资讯
介绍
欧洲艺术史提供了一种越来越有价值的批判语言,用于界定新媒体技术如何标志着我们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审美体验的深刻变化。其中包括反复引用巴洛克的形式雄辩来描述严重依赖数字美学的暴露癖的当代好莱坞电影所带来的视觉愉悦和观众表达方式(Cubitt,2004,2009;Klein ,2004 ; Ndalianis ,2004),2005 年,2008 年)。利用巴洛克的历史流动性,诺曼·M·克莱因(Norman M Klein,2004: 6) 认为,今天的“全球媒体和特效”为信息时代重新利用了最初在 1550 年至 1780 年间运行的普遍巴洛克语法,此后通过艺术和文化的“技术幻觉史”有力地转世。对克莱因来说,这些“有脚本的”视觉和戏剧效果(从 1955 年起)是“电子巴洛克”的例子,这个术语将当代电影的效果图像与建筑、雕塑、选美、全景、马戏团、主题公园、拉斯维加斯赌场、电子游戏和 21 世纪的艺术装置作为多媒体巴洛克幻觉工具,提供基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艺术规范的修辞娱乐体验。错视图像(第 15 页)。对于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2009 :50)来说,电子或“数字化”“新巴洛克”的现代阶段同样“以过度、景观和装饰的精致为特征,以至于它取代了传统的装饰”。结构原则成为文化生产的特征性形式财产”。这些展示品质无疑使巴洛克风格的语言非常适合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视觉风格的宽容,数字技术在流行的好莱坞电影中的出现往往以精湛的华丽为标志,再现了历史上巴洛克风格对过度和破坏的投资。推介会。
然而,新巴洛克美学在华特迪士尼工作室最近制作的数字动画和一系列九部计算机动画故事片中找到了另一个家,这些电影标志着该工作室与计算机图形学的最长不间断的接触。本文认为连续的电影《无敌破坏王》(里奇·摩尔,2012 年)、《冰雪奇缘》(克里斯·巴克和詹妮弗·李,2013 年)、《大英雄 6》(唐·霍尔和克里斯·威廉姆斯,2014 年)、《疯狂动物城》(拜伦·霍华德和里奇·摩尔, 2014 年) 《莫阿娜》(罗恩·克莱门茨和约翰·马斯克,2016)、《无敌破坏王:打破互联网》(菲尔·约翰斯顿和里奇·摩尔,2018)、《冰雪奇缘 2》(克里斯·巴克和詹妮弗·李,2019)《拉雅与最后的龙》(唐·霍尔和卡洛斯·洛佩斯·埃斯特拉达,2021 年)和《恩坎托》(贾里德·布什和拜伦·霍华德,2021 年)共同描绘了该工作室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阶段,可以理解为“迪士尼巴洛克”。在与数字技术的明确联盟的支持下,当代迪士尼动画长片展现了当代媒体和移动图像文化中许多相同的新巴洛克风格。饰演雷内·韦勒克 (1946:77)在讨论文学巴洛克及其同义词洛可可(一种过度装饰的风格,标志着巴洛克的最终表达)时指出,“每种风格都有其洛可可:晚期、华丽、颓废的阶段。” 2012年后迪士尼动画的风格和主题差异无疑标志着数字技术的一次有趣的转变,将隐藏、幻觉、干扰和“再现主义的文化方面”等主题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这些主题在历史上构建了巴洛克风格,现在又构建了新风格-巴洛克,美学(Egginton,2009:107)。
在数字化的原始视觉幻觉的高度支持下,迪士尼动画长片的这一阶段最终带来了一个思考更不规则(巴洛克)的机会。)工作室“晚期”风格的形状,探索这九部故事片如何设计基于特定(新)巴洛克诗学的剧变时刻。在此过程中,本文充分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含义,以及即使在讨论好莱坞工业参数内制作的流行动画时,将欧洲艺术史作为主导批判范式的中心意味着什么。当然,艺术史学中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和知识生产形式的局限性对于理解反映国际殖民势力的巴洛克艺术的具体政治史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中使用的“迪士尼巴洛克”标签承认了对巴洛克及其非欧洲和非西方“延伸”的全球性和殖民性理解(Ndalianis,2004:14),包括欧洲和南美洲和亚洲等不同地区对印度葡萄牙殖民地之间的循环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本文也承认艺术史在其方法上仍然主要以欧洲为中心,理所当然地需要文化和知识非殖民化,以重新参与巴洛克自己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地理,并防止进一步否认通过更严格的结构干预来保护少数群体社区。
迪士尼,艺术家
在《冰雪奇缘》的早期音乐剧《永远的第一次》中,隐居的艾莎公开加冕为阿伦黛尔女王之前,她疏远的妹妹安娜在欧洲艺术的形象中寻求安慰。她欣喜若狂地冲进城堡的肖像大厅,顽皮地向荷兰文艺复兴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重新诠释的《农民之舞》 (约 1569 年)中描绘的人物行屈膝礼,渴望地凝视着奥古斯特·塞鲁尔洛可可风格《野餐》中的男性英雄。1800 年代末,并在约翰·辛格·萨金特 (John Singer Sargent) 的《El Jaleo》(约 1882 年)的人群中跳起欢乐的安达卢西亚舞蹈。在众多的跨媒体邂逅中,安娜甚至跳到了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画作前《秋千》(约 1767 年)是巴洛克晚期的布面油画,也是迪士尼上一部影片《魔发奇缘》(内森·格雷诺和拜伦·霍华德,2010)的绘画洛可可风格的视觉灵感。当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以来,古典艺术对迪士尼动画电影的启发就已经广泛存在,包括晚期浪漫主义艺术家路德维希·里希特 (Ludwig Richter) 的影响以及古斯塔夫·多雷 (Gustave Doré) 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 19 世纪版画的影响。 David Hand,1937), Herman、Jean 和 Paul Limbourg 兄弟在《睡美人》 (Clyde Geronimi,1959)中重新构想的14 世纪Trecento风格,以及在《睡美人》中定义贝尔“乡野生活”有机美的浪漫主义风景。美女与野兽(加里·特劳斯代尔和柯克·怀斯,1991)(艾伦,1999;所罗门,2010)。1然而,《冰雪奇缘》中对弗拉戈纳德最著名作品的尖锐引用,本能地将扁平化风格和新古典艺术核心的“幻象喜剧”结合起来(Wellek,1946): 112) 与迪士尼原始的三维计算机图形相结合,从而可视化流行动画与古典艺术的碰撞,古典艺术经常引导对迪士尼动画长片的批判和文化探索。事实上,除了对迪士尼内部历史和批评周期性的贡献之外,本文认为在 2012 年后的迪士尼中明显体现的“新巴洛克”品质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耐用艺术的机会(在早期阶段就已开始) -迪士尼动画长片的历史叙述,已被用来批判性地识别工作室故事片之间的同质关系。
法国画家、插画家和壁画家让·夏洛 (Jean Charlot) 在《白雪公主》上映后不久于 1939 年夏天出版了这部作品,他是最早在古典和美术创作背景下审视传统动画技术的作家之一。夏洛特对迪士尼动画的热情评价,包含在《美国学者》的页面中杂志是他去年在工作室向迪士尼动画师和制图师发表八场特邀讲座的高潮,讨论了他们的艺术的表现系统和表现力。正是在这些讲座中——最终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版,也就是他去世大约 20 年后——夏洛特首次鼓励迪士尼员工“将自己视为现代壁画家,将伟大的设计投射到电影屏幕上而不是墙上”(丹尼,1999:143)。
夏洛特对迪士尼动画师在图形表现方面的技巧和理想的钦佩继续印刷,这表明他自己在“透视、绘图技巧、明暗对比和构图”方面的训练如何在迪士尼的流行艺术中找到了相似之处(1939:142)。在他多次提及修拉、塞尚、伦勃朗、莫奈、提香、普桑、乌切洛、莱热、格莱兹和格里斯的作品中,他挑衅地将西斯廷教堂比作唐老鸭,将米老鼠比作米开朗基罗,将白雪公主的医生比作拉斐尔的圣母,简短的米奇乐队音乐会(威尔弗雷德·杰克逊和沃尔特·迪士尼,1935 年)到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的“三维现实”(夏洛特,1939 年):260-270)。如果说早期以搞笑为导向的卡通片被定义为“原始”和“古老”的背景,并以“严肃”的黑白风格为标志,那么对于夏洛特来说,则是在比例、动作中发现的前所未有的光线和色彩细节迪士尼动画的幻想预示着媒体审美优先事项的发展。《白雪公主》富有想象力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动画新发现的“摄影渲染”能力,他得意地总结道:“我们已经看到七个小矮人从他们的洞穴中出现,进入夕阳,脱下平淡的哥特式制服,形成鲜明的对比光影文艺复兴盛期!(1939:269)。
夏洛特的评论是“有成就和善于表达的美术家的思想”(Denney,1999:141-142)在动画媒介中的宝贵记录,夏洛特的评论体现了美术与流行艺术之间惊人的智力合作,这是一个艺术史与现代大众融合的空间媒体,以及绘画空间的工艺和结构在工业卡通制作中找到了归宿。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和 1940 年代,通过与占主导地位的美术范式的联系而受到对迪士尼动画电影的尊敬的情况当然并不罕见。这种赞扬大部分来自知识界以及由评论家、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知识界,他们越来越被漫画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所吸引(沃尔特本人也被视为文化人物)。珍妮特·瓦斯科 (2001:119)承认“许多艺术评论家赞扬“艺术家迪士尼”,将他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勃鲁盖尔、伦勃朗和毕加索相比较”。例如, 《文学文摘》还在 1931 年报道过,“根据包括法国美学家和作家在内的一些‘高雅’欧洲评论家的说法,米老鼠确实是电影表达新世界的哥伦布”横跨英国、德国和匈牙利(Anon,1931:19)。在《新共和》后来发表的一篇题为“莱昂纳多·达·迪士尼”的文章中,政治漫画家大卫·洛 (David Low) (1942)迪士尼“不是作为绘图员,而是作为艺术家”。。。自列奥纳多以来图形艺术中最重要的人物。但这不仅仅是“西方传统的古代大师”。。。在 1930 年代迪士尼动画的批评中, “被最频繁地唤起”(Neuman,1999:250),但现代主义者也是如此,因为工作室的正式风格似乎成功地在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与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之间建立了桥梁。迪士尼的主要支持者是多萝西·格拉夫莱 (Dorothy Grafly),她在 1933 年将迪士尼与塞尚以及后来的毕加索进行了比较,因为他对构图和线条的灵巧处理使动画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Grafly,1933):337-338,迪士尼还与竞争对手弗莱舍工作室合作,庆祝超越“绘画局限性”的新艺术)。几年后,在对《匹诺曹》(Ben Sharpsteen 和 Hamilton Luske,1940)的评论中,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艺术评论家CJ Bulliet(1940:13)同样赞扬了“迪士尼台词与……之间的区别”。。。我们的“毕加索”的“抽象”是迪士尼的“抽象”绝对有效——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并且去做。
这些对迪士尼表演空间和视角、色彩和线条充满激情的框架,通过西方视觉表现传统,无疑再现了人们对“低俗文化”的熟悉欣赏。。。在高雅文化方面”(Smoodin,1992:133)。克里斯汀·汤普森 (1980:112)指出了动画评论家的长期传统,他们“将动画电影视为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将某些电影与其他文化上接受的艺术形式进行比较”。1930 年代迪士尼流行动画中常用的美术词汇最终证实了任何当代媒体的基本历史性,它们的“新”故事经常通过“旧”倒着讲述,以理解其作为文化对象的形式风格。早期动画话语中对既定艺术的转向同样体现了古典艺术原则与工业/审美现代性之间的推拉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支撑着迪士尼的动画,而且可以在整个工作室的多媒体事业中找到线索。史蒂文·瓦茨 (1997:41)将这种张力称为“感伤的现代主义”,这使得迪士尼能够在众多辅助媒体、休闲和消费品中不断融合“舒适的传统和具有挑战性的创新”。然而,这种高雅文化活动与低俗文化活动之间的碰撞——以及迪士尼在这一交叉点的瞄准——也演练了一种在(流行)文化生产的历史分析中常见的进化目的论叙事,即“早期形式总是”导致更完美的人”(Smoodin,1992:138)。这种关于进步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涉及从混乱和非系统的独创性到更加规范化的形式复杂性的“直接路线”,这是一条由繁荣的“黄金时代”和隐秘的“停滞”时期之间持续相互作用所支持的历史轨迹。或者,正如一位报纸记者在 1939 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白雪公主》的制作胶片和艺术作品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学家可能“很快就会将迪士尼的作品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引自Neuman,1999):251)。
迪士尼动画在流行的艺术史术语中通过“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传统三合一”来表述,承认新作品发展旧作品的假设,但也明确指出了通常存在的那种离散的时间顺序结构。 “紧紧抓住艺术”(Steele,2003:12)。感谢英国电影评论家兼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艾里斯·巴里 (Iris Barry),她“发展了动画的艺术史叙事”(Mikulak,1997: 57) 当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将商业卡通片纳入 MoMA 电影计划时,迪士尼的赛璐珞动画很快就与“艺术历史血统”产生了牵连。。。借助其在传统美术媒体(如素描和绘画)中制作的艺术品”(第 68 页)。然而,巴里——或者(1939年) 《白雪公主》展览的匿名评论家——几乎不知道艺术史分期的方法论倾向将成为迪士尼动画后续批评工作的支柱。像巴里一样,夏洛特 (1939)他本人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持开放态度,几乎立即将迪士尼纳入艺术史的掌握之中。他认为动画的“造型语言”已经开始遵循“艺术史绘制的图形”,通过提炼“原始、古典、巴洛克和颓废的风格”,相对较快地成为“自身完整的风格缩影”。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调查”(1939:268)。迪士尼的卡通(现在是电脑)动画长片已经被塑造成适应“早期、中期和后期”制作阶段的类似兴衰,工作室进行了大量跨学科研究,将迪士尼历史组织成连续的阶段或进化阶段,而不是让工作室的动画特征更具争议性和分散性。
迪士尼工作室(迄今为止)61部故事片的划分导致了离散的序列和电影周期的框架,根据代表性统一、工业动荡、创意停滞、公式化剧变和地震技术变革的时刻,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例如,迪士尼研究经常声称存在一个艺术雄心勃勃的“早期”时期,称为经典迪士尼,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众多迪士尼动画中流传的高雅美术范式的强烈推动。人们对迪士尼对动画的贡献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和审美稳定的“早期”时期有关,在这个时期,工作室对再现保真度的承诺达到了顶峰,因为它从短片转向了动画。无声卡通到长篇动画作品。随着动画越来越被认为是 20 世纪艺术的一种形式,工作室的绘画和制作艺术受到了艺术史学家、博物馆和画廊的关注,正是迪士尼“巩固了这种声望,将动画电影带入了当代”时代,有效地融合了美术、古典主义感和美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典范”(威尔斯,2012:236)。《白雪公主》和《奇幻森林》 (Wolfgang Reitherman,1967)之间发布的 19 部动画长片通过追求图像幻觉巩固了迪士尼作为动画表现标准的地位,产生了一套标准化的风格假设,这些假设合并成一套公式化的图形倾向。
迪士尼的绘画古典主义“早期”时期是“经典”,因为它不仅确保了好莱坞黄金时代动画的工业和经济可行性,而且为工作室自己的“超现实主义”(Wells,1998)情感设定了艺术标准。这种媒介与类似时期的艺术和文化一样,都渴望幻术主义作品的完美。在讨论 19 世纪欧洲艺术对迪士尼动画的影响时,罗宾·艾伦 (Robin Allan,1999:286) 认为“迪士尼艺术家崇拜拉斐尔前派,他们对自然世界的细节反过来又影响了迪士尼艺术家的严谨性。” 艾伦进一步指出迪士尼音乐剧《幻想曲》的“视觉密度”如何(詹姆斯·阿尔加等人,1940)植根于其“装饰艺术、新艺术和十九世纪学院艺术的分层纹理”(1999:275)。从查尔斯·布兰克-加蒂和音乐家音乐家到电影制片人和画家奥斯卡·菲辛格的现代主义几何学,《幻想曲》的无数视觉影响往往为迪士尼高度“欧洲”风味提供了蓝图,即使不是欧洲艺术对流行好莱坞的贡献动画更广泛。Kathleen Coyne Kelly(2012 :199)同样认为《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中中世纪风景的图像表现(Clyde Geronimi,1959)认为“就像”彩绘手稿或挂毯的绿色世界一样——无论是中世纪制作的还是拉斐尔前派等后来艺术家模仿的。具有影响力的维多利亚时代画家改革运动完全接受模仿和模仿自然作为他们的信条,借鉴浪漫主义的崇高新情感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社会艺术。献给约翰·坎梅克 (2017)然而,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角及其“视觉传达技术”对迪士尼动画师的影响(包括佛罗伦萨哥特式/原始文艺复兴画家乔托·迪·邦多内对迪士尼素描艺术家阿尔伯特·亨特的影响)反映了构图、线条如何和欧洲艺术的色彩充分保证了迪士尼自己的“古典”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品质。
对迪士尼工作室“生命幻觉”资质的批评往往源于他们将动画媒体超现实主义地“还原”为图形艺术,通过将动画据称预先确定的路线转向奇幻,从而取代了模仿的表现力。 ,抽象的,实验性的,非模仿的。尽管有强烈的反驳,“动画中现实主义的特权是有逻辑的”,特别是迪士尼通过“话语系统”改造“现实世界”,将古典绘画与“故事书插图、中世纪”结合起来。挂毯和彩绘手稿”(Kelly,2012:200)。然而,迪士尼盛行的超现实主义并不是通过消除动画的基本“魔力”来歪曲创造力,而是一套精心构建的正式原则,这些原则将成为整个 20 世纪美国商业动画的默认语言。对现实的转录恢复了——而不是反抗——动画作为拟像的潜力,并允许平等地考虑媒介表现的复杂性。因此,现实主义的经典结构并不是一条缺乏想象力、阻力最小的道路,而是一项极其精确和精确的事业,由于迪士尼在整个 20 世纪对动画媒体作为一种表现技术的复杂探索,
“迟到”迪士尼?
自这个基础性的黄金时代以来,迪士尼动画随后的高峰和低谷已经轻松地进入了“早期、中期和晚期”时代,这在 1930 年代被预测为迪士尼不可避免的未来。事实上,该工作室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早于艾米·M·戴维斯 (Amy M Davis, 2006)甚至可以称为“中年”(1967-1987),在 1966 年 12 月沃尔特去世后,迪士尼日益紧张的动画部门接受了新的管理。迪士尼“文艺复兴”时代(1989-1999)的出现也归功于迪士尼学者将其称为“第二个黄金时代”或“艾斯纳时代”,以确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对公司创意方向转变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中期”成为转瞬即逝的“停滞时刻”在下一个“黄金时代”成就之前。对 1989 年后迪士尼文艺复兴的文化理解是,它代表了迪士尼第一次文艺复兴结束 20 年后又一个公式化的稳定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植根于复兴和更新的话语,而是回归20 世纪 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古典主义的典型超现实主义风格。迪士尼动画长片的后续阶段同样可以通过迪士尼公式的想象来理解,该公式主要与“早期”古典时期相关,这反过来又使有关迪士尼品牌自我管理的更根深蒂固的问题浮出水面。图像。例如,克里斯·帕兰特(Chris Pallant,2011:111-125)提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立即进入的高度逆向和探索性的“新迪士尼”(1999-2004)阶段,在此阶段,工作室尝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细胞动画电影其特点是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它们与迪士尼公式的差异。这一时期之后是 2005 年后的“数字迪士尼”时代(Holliday,2019;Pallant,2011),随着工作室进入竞争日益激烈的好莱坞动画市场,卡通动画技术让位于计算机图形。当然,迪士尼动画长片的各个阶段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是绝对的或确定的。许多粉丝社区已经扩展了新迪士尼阶段,包括电脑动画电影《小鸡》(马克·丁达尔,2005 年)、《拜见罗宾逊一家》(史蒂芬·安德森,2007 年)和《闪电狗》(克里斯·威廉姆斯和拜伦·霍华德,2008),将这个更广泛的 1999-2009 时代定义为“迪士尼的后文艺复兴”、“迪士尼的第二个黑暗时代”或“迪士尼的实验时代”。迪士尼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只是增加了进一步的描述,作为通过文化生产语言(经典、文艺复兴、修正、更新、重启)来确定工作室细胞/计算机动画故事片的特定时期的一种方式(Mollet,2020))。因此,浏览一下对迪士尼周期性的流行和批评的描述——包括英国电影学院最近制作的“迪士尼电影史”(德特曼,2021年)——可以看到以下重叠的名称、阈值和间隔,以强化工作室的演变目的论:
1937–1967:经典迪士尼
1937–1942:黄金时代
1937-1959:古典时代
1943–1949:战时时代/包裹时代
1950–1967:白银时代/复辟时代
1967–1987:中学时期
1970–1988:黑暗时代
1970–1977:青铜时代
1989–1995:第二个黄金时代/艾斯纳时代
1989-1999:文艺复兴时期
1999-2005:新迪士尼
1999–2009:后文艺复兴/第二黑暗时代/迪士尼实验时代
2005 年至今:数字迪士尼
2007-2018:修正主义时代
2009-2013:复兴时代
2014-2017:重启时代
2009 年至今:复兴时代
这种根据“早期、中期和晚期”话语对迪士尼动画长片进行的映射和重新映射——以及艺术史工作中仍然至关重要的更广泛的分期问题——强化了爱德华所说的存在(2006:4)被称为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发现年表”。在萨义德对时间性如何整合创造力条件的人文分析中,萨义德围绕“晚期风格”得出的结论有效地勾勒出了历史和文化秩序或科学背后的重复轨迹,涉及创新的连续阶段(起源、意图、方法)、巩固(再现、连续性、连贯性)和偏差(修订、回顾、决议)。这些历时类别反映了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在《艺术形式的生命》(1992[1934])中提出的类别。:52),它同样概述了文化形式经历的四个阶段或“连续状态”:“实验时代,古典时代,精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福西永的文化变迁图式首次发表于 1934 年,与萨义德对成熟与衰落的关注相比,其生物性较少,尽管这位法国艺术史学家将巴洛克时期视为“放弃或改变了亲密礼节原则”的结束阶段(1992[1934]) : 58) 匹配迟到与巴洛克标准偏差之间的联系。早期风格既可以有积极的含义,也可以有消极的含义,预示着“衍生性、模仿性和不发达的技术”,就像“新鲜感、早熟的创造力、冲动和活力”一样(Hutcheon and Hutcheon,2016):55)。经典迪士尼时期(Pallant,2011:35-53,此后被称为“迪士尼形式主义”)无疑标志着工作室加强创造力和审美创新的早期阶段,这是开始迪士尼“项目”的迷人起源时刻”的方式并不完全归因于工作室早期的短片系列。
下一个“人类事件”或“第二大问题”统治文化——赛义德(Said,2006:5)称之为“从头开始的剥离”——是中世纪/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共同代表了工业和美学连续性战争的战场,尤其是在沃尔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去世之后。在工作室追求稳定性和连贯性的过程中,中年时期体现了一种短暂的偏差,最终被文艺复兴重新调整,重新包装了过去成功的形式。从《小美人鱼》(罗恩·克莱门茨和约翰·马斯克,1989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99 年 10 月上映的《人猿泰山》(克里斯·巴克和凯文·利马,1999),迪士尼文艺复兴已经巩固为一个十年的时期,其中古典表现的细致简单和图像形式重新出现,提醒人们长期存在的图形传统,尽管短暂地被遗忘。
这种“人类生活的总体假定模式”(萨义德,2006 :4)的最后阶段是“晚期风格”,这是萨义德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37)对贝多芬晚期音乐的描述中得出的一个概念,该音乐充满了疏离的特质,分离和距离。正是在这种“晚期风格”中,萨义德遇到了一种积极的“对抗”或矛盾、异议和解放的愉悦感,从而产生了“反映一种特殊的成熟、和解与宁静的新精神”的作品。 2006 年:5-7)。风格的迟到是对凝聚力和关系的挑战,是阐明文化形成中的差异和发现不连续性的结果,因此,以前曾被用来干预迪士尼动画的循环。Stefan Kanfer(1997:193)将《奇幻森林》称为“华特·迪士尼监督的最后一部长篇动画片,[它]展示了他晚期风格的所有属性和缺点”。在这里,“晚期风格”明确意味着迪士尼动画制作从经典阶段到中期阶段的过渡,标志着连贯风格衰落的最后几年(体现在沃尔特的艺术影响力减弱)以及对预定叙事和美学模板的远离。正如阿多诺本人所说,“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就是灾难”(引自Said,2006:12)。
然而,本文表明,当代迪士尼内部另一种创造性“晚期风格”的演变和出现植根于各个时期的结束和开始,这种风格将手绘技术的停止与好莱坞数字技术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包括将计算机图形学的工业和美学整合到迪士尼的细胞动画制作中。这里提出的“迪士尼巴洛克”是为了让人回想起迪士尼动画长片持久的艺术史叙事,同时也暗示工作室的当代故事片与“晚期”风格所熟悉的令人愉悦的巴洛克异议之间存在更广泛的联系。迪士尼的“迟到风格”远非植根于这种不守规矩的迟到带来的过剩、破产和疲惫,而是涉及一种更加令人愉悦的回旋或自信的变形,
连续制作的电脑动画作品有《无敌破坏王》、《冰雪奇缘》 、《超级英雄 6》、《疯狂动物城》、 《莫阿娜》、《无敌破坏王:破坏互联网》、《冰雪奇缘 2》、《拉雅与最后的龙》和《Encanto》毫无疑问,迪士尼将进入另一个产业稳定、创意繁荣和艺术发展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票房表现和评论界的好评,以及该公司以 74 亿美元收购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幕后支持。 2006 年(以及随后于 2009 年斥资 40 亿美元收购漫威,并于 2019 年斥资 524 亿美元收购 21 世纪福克斯)。艾莎·哈里斯(Aisha Harris,2016 年)在预示迪士尼“更丰富、更复杂的故事”时指出,“自从超级女权主义的《冰雪奇缘》以来,迪士尼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进步主义和对包容性的承诺不仅具有强大的力量,艺术决策,但有利可图的商业决策。2好莱坞商业媒体(以及几个在线讨论论坛)重新使用“第三黄金时代”、“新文艺复兴”和“复兴”等术语来描述 2012 年后的迪士尼动画长片,似乎旨在宣称回归到了古典时代的生产方法、意识形态统一性和风格原则。然而,这种对黄金时代白话的诉求最终使工作室早期的电脑动画长片(《小鸡》、《拜见罗宾逊》 、 《博尔特》)成为了过去,并且 - 由卡通动画长片《公主与青蛙》(罗恩)的发行分隔开来。克莱门茨和约翰·马斯克,2009)和小熊维尼(史蒂芬·J·安德森和唐·霍尔,2011)——指出了过去十年迪士尼在商业和评论界的具体复兴,童话故事片《冰雪奇缘》在国际上的成功巩固了迪士尼的复兴。
《时代》杂志的理查德·科利斯 (Richard Corliss,2014)在评论《大英雄 6》时将其称为迪士尼“最新的文艺复兴”,2012 年至 2021 年间发布的九部影片似乎明确表达了令人愉悦的异议和对传统的操纵,这些都是限制、不相容性的核心,以及晚期骨折。赛义德(2006:12)谈到了在审查迟到时面临的一个明显的挑战,即“试图说出是什么将作品结合在一起,赋予它们统一性,使它们不仅仅是碎片的集合”。由两部以神话王国为背景的童话公主故事片、两部发生在电子游戏内的兄弟喜剧、一部寓言唐纳德·J·特朗普时代种族政治的拟人化警察电影、一部结合了美国和日本国家的超级英雄漫画改编而成一部植根于波利尼西亚神话的冒险音乐剧和一部受东南亚和哥伦比亚文化启发的两部奇幻作品,2012年后迪士尼动画的异质性表明了一种异常现象,使得很难找到叙事或风格上的共性。而前六部迪士尼影片中的五部(小鸡小鸡之间)2005 年的《冰雪奇缘》和2011 年的《小熊维尼》都是根据已有的文本改编的,2012 年之后的九部影片中只有四部改编自早期的资料(冰雪女王的《冰雪奇缘》 / 《冰雪奇缘 II》;漫威漫画的《大英雄 6》 ;和毛伊岛骗子人物莫阿娜)。《无敌破坏王》、《疯狂动物城》、《无敌破坏王》、《拉雅与最后一条龙》和《Encanto》都是原创故事,而其中两部(《冰雪奇缘 2》、《无敌破坏王》))是续集,尽管许多续集位于更广泛的附属媒体产品(短片、电视剧)跨媒体网络中。这九部影片中只有四部也是音乐剧(《冰雪奇缘》、《莫阿娜》、《冰雪奇缘 II》、《魔法幻影》),仅比高度分化的新迪士尼时代多了两部。3还有几个引人注目的设计元素。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影响,Shiyoon Kim 在《大英雄 6》中的角色设计以及电影中旧金山和东京建筑的融合(创造了“San Fransokyo”)让人想起迪士尼的《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Gary Trousdale 和 Kirk Wise,2001 年),改编自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灵感来自漫画艺术家迈克·米格诺拉 (Mike Mignola) 的扁平化图形描绘。米尼奥拉在《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中的设计被迪士尼动画师标记为混合“Disnola”风格,反过来又让人想起英国漫画家杰拉尔德·斯卡夫(Gerald Scarfe)作为概念人物艺术家对早期大力神(罗恩·克莱门茨和约翰·马斯克,1997)的作品,他的贡献从而产生了一部类似“非典型”的混合电影,“一半是围巾,一半是迪士尼”(Wells,2002:145)。
巴洛克风格似乎不仅有助于理解迪士尼“后来的”电脑动画电影的风格和叙事异质性,而且有助于理解如此多样化的群体(包括他们的与其他电脑动画电影的联系,请参见Holliday,2018)。巴洛克一词带有根茎迷宫和多维空间、运动自由、自我意识过剩、互文性、相互关联性和序列性等内涵,最终感觉适合《无敌破坏王》庞大的电子游戏环境的规模和奢华。《大英雄 6》中的跨文化旧金山京城一切都穿着未来派的霓虹灯,《莫阿娜》、《冰雪奇缘》电影和《拉亚与最后的龙》中对海洋、冰和水滴的华丽展示,让人想起巴洛克观赏花园文化的核心水戏法 ( giochi d'acqua )在意大利,水被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喷泉工程师 ( fontanieri )“引导、分开、转向、驱动、拦截并使其上升或下降”(Tchikine,2010:57)。
然而,巴洛克风格被指定为电影和故事的描述符,这些电影和故事明确地突出了非欧洲有色人种的遗产和经历(从《莫阿娜》中的波利尼西亚和《大英雄6》中的日本,到《开斋节和最后的世界》中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龙》和《恩坎托》似乎冒着方法论上回归艺术史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风险。然而,从文艺复兴后欧洲艺术和文学的起源出发,对巴洛克风格的持续“批判和重新定义”已经对其作为“欧洲中心概念”的身份提出了挑战(Salgado,1999):316)。当然,直到 1800 年代初,巴洛克风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包括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运动都充分提醒人们剥削性的殖民计划及其征服叙事。但它们同样是殖民时期该风格通过地区/当地艺术家和传统进行重新语境化的指标,这很快使巴洛克“对大都市学派或风格的明显忠诚”变得复杂化。事实上,萨尔加多认为“混合改造”是殖民主体“文化抵抗和生存”能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随着欧洲习俗移植到“殖民地地区”,通过“秘密插入或嫁接“被否认的”文化元素”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种族混合体,而这些文化元素据称被即将到来的“欧洲高级风格”所否认或取代(第317页)。尽管这是“外来形态与本土形态在冲突中痛苦且不协调的重叠”的结果——风格上的冲突在《大英雄 6》脉动的组合美学——本土转移、劳动和征服的相同条件,即使不是其异议、反霸权和开垦的政治,也对(拉丁美洲)巴洛克的去中心化艺术风格和跨文化杂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在迪士尼动画长片的背景下谈论巴洛克情感,并不只是简单地确定“后来”的艺术和文化史上与欧洲“高雅风格”毫无争议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定时期。相反,它是要认识到一个已经从历史和地理特殊性中适当解放出来的术语,并且通过遵循其破坏性的殖民谱系,使其与一系列艺术和文化现象的相关性始终具有流动性。安吉拉·恩达利亚尼斯 (2005:86)认为“巴洛克不仅仅是位于十七世纪(其传统的、暂时的家园)内的一个特定时期”,而且以“跨越历史分期界限的形式品质”的范式运作。这种非时间性的条件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巴洛克风格具有持久的维度——转向“自我反思、精湛技艺、戏剧性、奇观、展示”(Ndalianis,2008):269-270)——也许可以解释它最近在流行的好莱坞电影中超媒体化数字奇观的应用。因此,2012年后的迪士尼动画长片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当代媒体文化的众多“新巴洛克风格”之一,其修正和回顾的“晚期风格”,一个与国家历史中心的光学展示充分结合的空间。巴洛克对幻觉主义的态度和新巴洛克的情感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体技术。
“迪士尼巴洛克”
《无敌破坏王》是“迪士尼巴洛克”的首部故事片。影片通过“故障”的实践,正面面对数字美学的不完美的不稳定性和表面性,“故障”是一种技术故障,通常标志着数字文化和计算机媒介传播的错误。电子游戏角色 Vanellope von Schweetz 是一个电脑动画化身,她与破坏性、不稳定的力量作斗争,这些力量将她的本体论构建为一种技术幻觉。她那出问题的身体——被角色假装成一种“像素阅读症”——是一种根本性的痛苦,干扰了她作为媒体制品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使她与同时代的卡通人物(虚构人物中的化身)完美的视觉错觉形成鲜明对比。电影中的游戏《Sugar Rush》)。诺尔·卡罗尔 (1988:297)观察了现代艺术理论中的反幻觉主义论战如何成为“诸如“逼真”,“模仿”,“模仿”,“拟像”,[和]“复制品”等古典幻觉属性的解药。 。Vanellope 是“现代的”,因为她陷入了变革性的“还原主义计划”,通过公开虚拟表示的技术参数,将计算机图形剥离到其“基本成分”。《无敌破坏王》中的云妮洛普在算法和代码层面上处于不稳定的衰退状态,她的作用是“提醒人们机器的不完美、嘈杂、有损本质”。。。[这]违背了我们当代数字文化对技术提供秩序的实证主义信念”(Hainge,2013:129)。Vanellope 是一种正式而混乱的骚动,它通过反射性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作为技术外观的本体论上,从而取代了数字照片写实主义记录的不可见性。
正是在这种关于错误和失败、故障和不幸的话语中,小故障最终成为巴洛克风格的一种姿态。Michael Betancourt (2017 : 58) 认为:
当故障成为巴洛克式的爆发时,示范性的生产过剩,除了简单地中断生产流程之外,它还可以呈现装饰性浪费生产的特征,这种位置使故障超出了资本主义允许的功能范围。
巴洛克风格的不确定性在意大利语术语“statuino”中得以体现,这是一个 17 世纪的新词,“让人联想到艺术家在发明或创作绘画、素描甚至版画时应努力追求的完美,而这种缺陷会损害完美”。。。[它]揭示了巴洛克完美美学核心的内在振荡和矛盾”(Pericolo,2015:863)。《无敌破坏王》中出现故障的云妮洛普的数字成就操作“脚本化”幻觉的自我意识时刻,这些时刻属于克莱因的“电子巴洛克”,其中包含流行的视觉特效技术。因此,云妮洛普是一种巴洛克风格的点缀,在影片中被记录为一种技术断裂或干扰,一种越界的、变革性的不守规矩的力量,表达了身份、归属感和对预先设定的角色的不满的问题。事实上,云妮洛普引发了个人与数字世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一点在续集《无敌破坏王:破坏互联网》中得到了强化。云妮洛普闯入另一款游戏(大逃杀风格的“屠杀竞赛”)破坏了整个虚拟空间的稳定。计算机病毒复制了云妮洛普的故障(她最大的不安全感),触发服务器重新启动,导致她周围的计算机图形崩溃。《无敌破坏王》坐在电子巴洛克的现代“技术幻象”军械库中,唤起了巴洛克剧院的技巧,同样对新数字动画提供的骗局的荣耀感到高兴。正如克莱因(Klein,2004:51)所说,“类似于巴洛克风格的透视扭曲,一个小故障”。。。揭示了电影制作的装置。这是一个揭露。云妮洛普在《无敌破坏王》中的出场标志着最终三维计算机渲染的突破,这一时刻提供了观念的转变,超现实主义的“古典主义”暂时“出错”了。
《无敌破坏王》还通过云妮洛普建立了对“迪士尼巴洛克”的关注,其主题包括隐藏、幻觉和干扰,这些主题支持巴洛克对“再现主义的文化方面”的投资(Egginton,2009:107)。正如巴洛克对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反应,标志着“从旨在尽可能忠实地模拟现实的表现主义和对应艺术、绘画、建筑或雕塑的决定性转变”(Glazier,2020:163),迪士尼已经开始全面对数字幻觉主义有一种更加反思性的理解。2012 年后的秘密或“扭曲”恶棍循环,包括 King Candy/Turbo(《无敌破坏王》))、助理市长道恩·贝尔韦瑟(《疯狂动物城》)、罗伯特·卡拉汉(《超级英雄 6》)和特菲蒂(《海洋奇缘》)并没有通过角色设计和表演公开地标明他们是敌对的,而是作为叙述的反身性侵犯的一部分而被揭露为两面派。的期望。《冰雪奇缘》对这一比喻的运用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一部重新塑造相对稳定的公主叙事模式的电影《冰雪奇缘》,再次由展示和讲述的多个主题构成。艾莎从小就隐藏在阿伦黛尔王国之外,她的妹妹安娜对她的水动力、心灵遥感和魔法能力不了解。然而,后来“迷人”的汉斯王子被揭露为两面派,而不是安娜的真爱对象,这标志着对邪恶揭露的反射性处理,通过符合经典迪士尼王子英雄主义传统的视觉编码来获得影响力。巴洛克“可以被视为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的逻辑延续和延伸,有意识地强调和“变形”常规技术”(丹尼尔斯,1946:117)。冻结的情况下汉斯王子的揭露成为了巴洛克的一种姿态,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有意识的“变形”和对公式叙事安全性的偏离,以此强调他的欺骗的风险。
这些有趣的隐藏和伪装模式的参与是“巴洛克掩盖的一部分”(Klein,2004:4),反映了巴洛克对伪装的乐趣和伪装的幻想的某种态度。安德烈斯·佩雷斯-西蒙甚至将《莫阿娜》对真理和合法性的不同寻常的态度——体现在螃蟹塔马托亚(Tamatoa)所演唱的有关甲壳类动物装饰性外壳的音乐剧《闪亮》中——与作家威廉·埃金顿(William Egginton)(2009:144)关于新巴洛克美学的作品并列。传统和“表象与它们表面上所代表的世界的关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迪士尼影片则强调真实性(阿拉丁的真理是“未经加工的钻石”;辛巴的命运是《骄傲摇滚》的“真正的国王”)。《狮子王》,罗杰·阿勒斯和罗布·明可夫,1994),《莫阿娜》代表了“华特迪士尼工作室发展轨迹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因为它完全拥抱了外表的肤浅和人为(Pérez-Simón,2009:79)。除了庆祝《无敌破坏王》中“失控”的云妮洛普之外,塔马托亚的歌曲还强调了过度的戏剧性和场面调度的表面效果。这些价值观可以与巴洛克更广泛的“实验”联系起来,其表现形式“似乎总是牌面朝上”。。。从而通过一种特殊的隐藏方式来展示其艺术对象”(Glazier,2020:163)。莫阿娜就此安息,为佩雷斯-西蒙 (2009:74-80),关于巴洛克美学的悠久历史,特别是像不稳定且技术化的云妮洛普一样,电影如何成为“断裂”,“将我们带回巴洛克人物角色、面具的概念化”。除了名副其实的“蒙面”反派糖果王、罗伯特·卡拉汉和特卡(他们各自都隐藏在别有用心的身份和虚假相貌后面)之外,《莫阿娜》中对披露的有趣处理有助于立即识别在“迪士尼巴洛克风格”中运作的反幻觉主义品质。 '。
巴洛克风格的辉煌、多样性、复杂性和碎片化在计算机生成图像的成就中也找到了类似物。很难想象艾莎在两部《冰雪奇缘》电影中华丽的冰雕、 《大英雄 6》中的多态微型机器人(自主机器人,其机械多功能性使其能够构建复杂的空间结构)、变形的无定形德鲁恩和散发的光束从《拉雅与最后的龙》中的龙珠到包裹着库曼德拉,或者包裹着恩坎托的神奇房子“小屋”的甘美蓝花楹和九重葛花,没有计算机图形学的可能性。Cubitt(2004 :228)以当代电子巴洛克时代及其数字介导的奇观时刻为框架,进一步描述了新巴洛克虚拟摄影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充满了增强的“矢量运动”,从而产生了屏幕的装饰性结构。空间。夏洛特在 1930 年代末的著作中已经将巴洛克风格牢牢地扎根于摄影机移动的可能性之中,他指出“巴洛克风格的思想——希腊人、马格纳斯科、杜米埃——在静态媒介中工作,但被动态所困扰,会欢迎电影摄影”(1939:268)。鉴于动画的基本“特殊”效果是运动效果,Klein (2004:248)甚至将动画本身定义为“将巴洛克风格的错视或变形转变为移动图像的艺术”。然而夏洛特(Charlot,1939:261)声称,与“经典的僵硬线条”不同,“巴洛克大师在运动中走得最远——使用混乱作为构图规则”。在整个“迪士尼巴洛克”中,数字辅助舞台技术的存在利用了视角和方向的情感品质,从而与计算机动画空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相遇。《拉雅与最后的龙》的魔法与武术叙事为精心设计的序列提供了背景,邀请观众惊叹于数字合成镜头的深度、维度和细节(特别是在熙熙攘攘的塔隆市的动态逃亡中,以及后来在拉亚与德鲁恩的最后对峙期间),而《大英雄 6》以数字长镜头达到高潮,将英雄主角们在旧金山的混合建筑中奔跑、飞行、滑冰、跳跃和滑翔时联系在一起。在《冰雪奇缘2》中,俯冲镜头同样起到了连接作用,在虚拟地理中移动,标志着从开场序幕到当今阿伦黛尔的过渡。在城堡的阳台上找到艾莎女王后,镜头跟随一片秋叶的偶然旅程介绍了安娜姐妹,该装置似乎是一种看不见的引力的受害者,引导着它华丽的运动。
正如巴洛克形式“倾向于从各个方向侵入空间”(Focillon,1992[1934]: 58),“迪士尼巴洛克”的虚拟摄像机通常不再受角色代理的驱动。相反,它导航的动画空间现在是开放和无限的,立即以a为中心,没有明确的前景或背景动作平面。作为巴洛克视角“出错”的物理化姿态(相对于古典的“封闭”系统),虚拟摄像机围绕三维空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近似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迪士尼多平面设备的空间效果,该设备广受赞誉。一项巴洛克发明,正式记录了动画环境的体积深度。然而,随着工作室在文艺复兴时期引入 CG 图像和流程(包括采用数字水墨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和 Deep Canvas 软件),这种矢量移动技术得到了强化。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数字视觉特效逐渐融入迪士尼动画长片,提供了巴洛克风格的点缀,提供了侵入性“混乱”的时刻,通过令人愉悦的变形正式扰乱了“经典路线”,从而创造出“在,但奇怪的是与现在不同”( Said,2006:24)。
在《美女与野兽》的标志性数字视觉特效场景中——美女与野兽在镀金的城堡舞厅中跳舞——观众在虚构世界中的过度(重新)定位向这种隐秘的本体论和视觉顺序。虚拟摄像机突然从地面位置移动,从大理石地板上升到金色吊灯,拍摄舞厅天花板上的壁画。虽然这幅错视画模拟了空间的延伸,但相机的失重和向上移动同样反映了巴洛克透视天花板艺术品中常见的“飞行幻觉”(Ndalianis,2004年):90-91)。在这个序列中富有表现力的摄像机放置无疑提供了城堡盛期巴洛克内部的特写镜头,将观众带入和带出数字动画环境。但是,通过提供如此优越的有利位置来欣赏其细致的凹槽、拱门和柱子,《美女与野兽》最终为观众提供了巴洛克动画空间的新巴洛克体验。
垂直性和丰富性的数字美学体现了巴洛克对多中心主义和连续性的迷恋,这符合迷宫的隐喻。在虚拟摄影机的巨大支持下,“迪士尼巴洛克”提供了深入了解幻觉虚拟空间的边界和距离的电影。正如福西永(Focillon,1992[1934]:67)所说,巴洛克揭示了“系列系统”——一个由轮廓分明、节奏强烈的不连续元素组成的系统。。。[那]最终成为“迷宫系统”。拉尔夫打破了互联网也许最能体现这些巴洛克式的迷宫特质,不仅发生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而且发生在万维网中。电脑游戏和互联网都是某种新巴洛克多样性、多中心主义和多线性的文化象征(Ndalianis,2004:27)。作为连续剧的形式,互联网的网络空间在《无敌破坏王:打碎互联网》中被形象化通过对流行文化图像的根茎式探索,拉尔夫和瓦内洛普穿越了通信线路、互联网品牌、大数据公司(亚马逊、eBay、谷歌)、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Twitter)、媒体图像和知识产权(IP)(皮克斯、漫威)塑造了创作者和授权者的数字乌托邦。巴洛克风格通过“复制”实现连续性的倾向在影响拉尔夫的复制粘贴痛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拉尔夫在电影的高潮期间成为了一个可繁殖的计算机病毒,“破坏了互联网”。变体拉尔夫像《大英雄 6》中层叠的微型机器人一样聚集在一起,让人想起构建虚拟本体的像素群(也许还有好莱坞特许经营心态的繁殖序列逻辑),或者《Encanto》中神奇的伊莎贝拉·马德里加尔(Isabella Madrigal)将有感知力的五月花和茅膏菜花幻化成各种形状,累积起来构建出一个耸立在数字媒体内容网络上的巨大聚合体。
在“迪士尼巴洛克”的对立面,《无敌破坏王》和《无敌破坏王》都反映了新兴的品牌协同电影,其强化的互文策略和猖獗的娱乐基础设施的叙事化。他们提高的媒体素养和流行文化文物的积累使他们与自“迪士尼巴洛克”时代开始以来发布的几部数字动画长片(以及具有大量数字视觉特效的真人电影)齐名,这些电影都对迷宫般的品质进行了不同的投资。基于 IP 跨界视觉享受的当代娱乐产业:《乐高大电影》(Phil Lord 和 Christopher Miller,2014 年)、《蜘蛛侠:平行宇宙》(鲍勃·佩尔西凯蒂、彼得·拉姆齐和罗德尼·罗斯曼,2018 年)、头号玩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18 年)、空中大灌篮:新遗产(马尔科姆·D·李,2021 年)、猫和老鼠(蒂姆·斯托里,2021 年)、自由人(肖恩) Levy,2021)和Chip 'n Dale:救援游骑兵(Akiva Schaffer,2022)。拉尔夫打破了互联网在他自己的连续动作和重复的多中心移动性(包括拉尔夫对自己形象的过度复制)中,以云妮洛普为主角的一个序列尤其引人注目。在迪士尼庞大的媒体目录中,这位熟练的视频游戏赛车手遇到了工作室动画史上的多位迪士尼公主。迪士尼作为多媒体集团的地位以及与皮克斯的紧张劳资关系(莫阿娜和安娜承认他们“无法理解”《勇敢传说》、马克·安德鲁斯和布伦达·查普曼,2012 年的苏格兰公主梅里达,因为她“来自其他工作室”),这一场景的喜剧色彩来自于迪士尼对其过去媒体产品的回顾,同时也开玩笑地承认了自己品牌的重复。
该序列在对经典公主的互文引用中部分回归古典主义,作为一种重复的策略,受到早期“风格主义”情感的影响,这标志着工作室的第一轮电脑动画长片。连接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与巴洛克时期的一个阶段,《小鸡》、《博尔特》和《拜见罗宾逊一家》中所确定的反幻觉主义的“风格主义”喜剧(霍利迪,2018:205-223)在“迪士尼”中得到了充分实现。巴洛克风格是迪士尼(艺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正如 EBO Borgerhoff (1953 : 326) 所说,“矫饰主义是对规范的表现性偏离;巴洛克风格是对常态的回归,但是带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情感色彩,并被继承和同化”。《拉尔夫》打破了互联网对其古典风格的“色彩”,它对迪士尼公主的处理更接近巴洛克风格的回归,而不是矫饰主义的偏差,重新塑造了几个卡通动画角色(白雪公主、灰姑娘、奥罗拉、爱丽儿、贝儿、茉莉花、风中奇缘、花木兰、蒂安娜)在三维计算机图形中,同时将其他电影中的其他人(长发公主、安娜、艾尔莎、梅里达、莫阿娜)作为其多媒体交叉的一部分(类似的互文性时刻出现在《疯狂动物城》中,其中包括“迪士尼巴洛克”电影《无敌破坏王》、《大英雄 6》、《莫阿娜》的海盗家庭媒体副本的序列,《冰雪奇缘 2》以拟人化游戏《Wreck-It Rhino》、《Pig Hero 6》、《Meowana》和《Floatzen 2》出售。对于Ndalianis (2004 : 88) 来说,“当引用成为重写过去的工具时”,新巴洛克风格就出现了,就像重复的结构和变形模式定义了萨义德晚期风格的注释一样。在《疯狂动物城》和《无敌破坏王:破坏互联网》中,明确暗示迪士尼自己的媒体目录“开放”而不是“关闭”,作为其不断扩大的多中心主义和巴洛克补救措施的一部分。就像《冰雪奇缘》中汉斯的隐藏和伪装一样,其结果是一个互文的迷宫,迪士尼动画已经开始大力折叠起来。
结论
巴洛克的跨历史逻辑使新巴洛克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变革中扎根,其中包括娱乐集团及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后现代主义多媒体娱乐企业和全球化信息时代。触手的范围越来越大。然而,在 17 世纪,“资本主义和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是巴洛克形式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Ndalianis,2004 年): 26),它在当代媒体文化中的重新出现标志着技术与全球化的交汇点,在媒体聚合时代引发了扩张和越界的工业背景。然而,对于迪士尼动画长片的内部周期性,巴洛克扮演着更为温和的角色,保留了工作室与艺术史的长期批判和文化关系,同时将数字成像技术的装饰应用置于其“后来的”计算机动画长片中牢固地融入当前分歧和分化的媒体环境中。当代好莱坞仍然是一个日益巴洛克式的工业体系,植根于讲故事的乘法和模块化结构(续集、连续剧、衍生剧、重新启动、翻拍),其特点是越来越愿意接受错综复杂的叙事潜力,包括分叉路径、聚合时间线以及重叠的虚构宇宙和多元宇宙。这种商业要求和管理策略是“当代娱乐媒体所采取的方向的典范”(Ndalianis,2004:23),但同样揭示了来自巴洛克时期的词汇如何坚持帮助理解电影复杂的技术繁荣和过度发展。除了商业盈利能力和持续的评论界声誉之外,迪士尼发行的《无敌破坏王》和《Encanto》之间的九部电脑动画电影标志着一些不同的、更不和谐的事情,反过来又成为好莱坞市场力量的旗手,而好莱坞市场力量是由经济上成功的电影推动的。新巴洛克式的称呼方式。然而,对迪士尼第 61 部也是最新一部动画长片——原创电脑动画科幻冒险片《奇异世界》的评价褒贬不一。(Don Hall,2022)——加上票房表现不佳,在撰写本文时,预计工作室将损失近 1.5 亿美元(McLintock,2022;Rubin,2022)——暗示另一个时期可能到来迪士尼动画部门的“停滞”,如果不是早期证据表明某些创意偏离了过去十年发展和完善的巴洛克风格。虽然现在规划迪士尼动画长片的未来还为时过早(特别是考虑到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 (Bob Iger) 于 2022 年 11 月回归幕后取代鲍勃·查佩克 (Bob Chapek)、迪士尼+作为流媒体平台的持续扩张以及好莱坞更广泛的业务)正如拟人化的管家科格斯沃斯在《大流行后》时期的产业调整所描述的那样美女与野兽在参观野兽城堡的“极简洛可可式设计”时,“如果它不是巴洛克风格,就不要修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