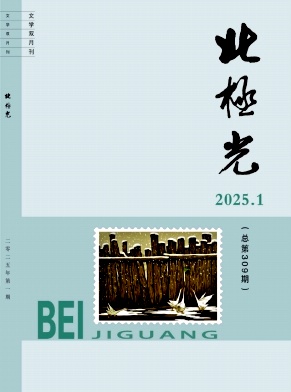新闻资讯
介绍
本文重点介绍 20 年代韩国女医生先驱之一李图教 (1897-1932)。她还是以女性为特定目标受众的医学知识的重要普及者,也是韩国新生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易活跃于社会的八年(1924年至1932年)中,她发表了数十篇期刊文章,涉及许多与医学、卫生、性别平等以及异性和同性恋亲密关系有关的问题。然而,她最重要的杰作最终是她自己的生活——本文将尝试利用所有可用的证据来勾画和分析她的生活。
尽管易对韩国医学界早期女性史和韩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历史都很重要,但除了韩国一位主要专家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韩国殖民时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热门文章外,没有专门的研究(我是,引文2019年),目前已发表在 Yi Tǒgyo 上。这正是本文旨在填补的空白。李桃教是一位护士出身的医生,也是韩国现代医学史上最早受过日本教育的女医生之一。本文重点介绍了她作为一位开创性的、以女性为导向的医学知识普及者的角色,她具有强烈而清晰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观点。同时,本文强调了伊托教的革命生活实践: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她毕竟是 20 年代为数不多的几位女医生之一,她们最终牺牲了成功的职业生涯,并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服务于激进的解放事业。本文将试图探讨易的专业见解如何对人类心理、性、或生育与她对激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愿景以及她的女权主义观点有关。它将特别强调她对异性和同性恋亲密关系和婚姻生活的态度,同时探讨像易一样激进的当地医生和作为现代医学特权主导主体的日本殖民当局之间复杂的冲突与合作模式。和卫生政策。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易的许多著作,大部分是为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的韩国报纸和期刊撰写的。易氏开展医学知识普及运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是日本殖民总督每日新保的官方喉舌。除此之外,李易的关于医疗和性别与家庭相关问题的文章可以在几家韩国私营报纸和期刊上找到,包括《Tong'a Ilbo》(成立于 1920 年)、《Chungoe Ilbo》(1926-1931 年)、《Pyǒlgǒngon》 (1926–1934) 和Samch'ǒlli (1929–1941)。
一般来说,医学和卫生专业人士的普及性贡献受到现代韩国媒体的欢迎,因为公众对更“科学”的人体和日常生活方法越来越感兴趣,因此此类出版物受到公众的积极追捧。这些著作脚注1涉及多种话题,重点关注日常生活卫生和疾病预防,包括专业人士对冬季戴防护口罩或预防胃癌等问题的建议。
然而,所有殖民时期的出版物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脚注2它们需要使用女权主义阅读技巧(Walters,引文1995年,第76-79页)来自一位当代韩国女权主义思想研究者(如本文作者)的正确分析。这项技术使研究人员注意到“庞大而复杂的关节回路”(Walters,引文1995 年,第 17 页。14)既先于文化文本,又出现于文化文本之后(不仅包括书面叙述,还包括视觉作品,例如电影或电视剧)。它是特定文化文本或文物的互文内涵、它在当代辩论中的地位,以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述和话语,定义了文本或文物的最终含义(沃尔特斯,引文1995年,p。18)。必须注意作者只能稍加暗示的语境,注意那些无法明确展开和阐述、只能潜伏在字里行间的叙述,注意题材和重点的选择,并与这些内容进行比较。其他作者的选择,例如更保守的韩国和日本男性,这可以间接表明作者的真正兴趣和担忧。本文使用的其他来源包括日本警方、报纸和韩国印刷媒体对易的多种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当代报道。综合起来,
像易的信念和地位的反殖民活动家能够与殖民地医疗机构合作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殖民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对生命政治的规范性理解。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是指现代国家对其主体生存的生物条件(包括日常卫生、性和生殖)行使权力。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国家开始编制相关统计数据,同时利用其对公共卫生、健康和生殖的责任来使其扩张的权力合法化(福柯,引文1997 /引文2003 年,第 242-244 页;另见巴顿,引文2016)。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基本同意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例如,由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合法性的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应该以有组织的、集中的方式调节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生物学基础。时尚(普罗佐罗夫,引文2016)。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易为代表的所谓解放的现代主义计划与殖民当局的压迫性现代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并非不可想象。此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易烊千玺并不仅仅局限于医学知识及其普及领域,她还积极介入女性的日常生活和权利、性别关系、亲密关系等问题。她的社会政治活动是本文的另一个焦点。然而,在讲述李伊作为医生和社会活动家一生的主要事件之前,我们需要审视一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话语及其在20世纪20年代韩国的驯化轨迹。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传入韩国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是解决“妇女问题”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解放方法。随着 1880 年代后妇女解放斗争的加剧,女性就业和教育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对妇女也应该从新兴工业大众社会的更大包容性和民主化的总体趋势中受益的更高期望的氛围,这种方法成为最重要的。霍布斯鲍姆,引文1987年,第 200–204 页)。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制度的阶级决定性质的见解,婚姻制度允许沿着父系继承私有财产,确保丈夫在资产阶级父权家庭框架内的统治地位。即使这样的家庭是建立在形式上“自由”、自愿缔结的婚姻的基础上,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始人恩格斯(1820-1895)提出的逻辑,它也并不比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本质上不平等的关系更自由。 ,考虑到男性对家庭收入来源的控制。虽然恩格斯希望妇女的经济独立——她们进入“公共工业”领域将使她们能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追求与异性的关系(恩格斯,引文1884 /引文2004 年,第 65-80 页),列宁(1870-1924)走得更远,认为只有家务劳动(已婚妇女的主要负担)的“社会化”才能为她们的解放提供必要的先决条件(列宁,引文1919 /引文1965 年,第 432-434 页)。这一立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惯例的“上层建筑”的首要地位的观点,与妇女参政论者相信妇女的核心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妇女获得选举权以实现她们的解放(Mayhall,引文2003 年,第 12-24 页)。
对社会经济决定论的信仰并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者对性别关系更亲密的一面的兴趣。例如,恩格斯希望两性之间的经济平等最终会导致仅基于“真爱”的关系和同居,并且只要双方继续维持这种关系的愿望消失,这种关系和同居就很容易消失(恩格斯,引文1884 /引文2004 年,第 86-87 页)。同样,倍倍尔(1840-1913)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女性与男性完全平等,完全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爱情对象,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缔结和解除亲密关系(倍倍尔) ,引文1879 /引文1904 年,第 342-349 页)。不过,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亲密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俄罗斯女性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柯伦泰(Kollontai,1872-1952)做出的。1920 年代初,柯伦泰在苏联国家及其外交部门担任要职(她是世界外交史上最早的女大使之一),同时创作了几部小说,以一种相当反传统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革命的亲密关系。其中一部小说, Vasilisa Malygina(翻译成英文为《红色爱情》)(1923 年;另见 Kollontai,引文1923 /引文1927年),讲述了两个共产党人的爱情和婚姻的火热故事,同名女主人公瓦西里莎最终自愿退出现有的长期关系(尽管她怀孕了),理由是她伴侣经历了不可挽回的意识形态和性格变化,使得昔日的同志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不再可能。该书于 1927 年被翻译成日语,1928 年被翻译成韩语,1929 年被翻译成中文,向东亚(包括韩国)的读者介绍了一种非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亲密关系方法(Barraclough 等人,引文2015)。
鉴于自 192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直在韩国发展,柯伦泰讲述了一个获得解放的妇女拒绝结婚或同居,除非这种关系以相互尊重和友情为基础的关系,因此受到韩国公众的热切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普遍传播同步。1924 年 5 月,第一个社会主义妇女活动家组织出现,名为“朝鲜女同志协会” 。其纲领“建设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社会”和“妇女解放运动”,其意识形态方向不容置疑(Cho,引文1990年;崔和孙,引文2020 年,第 154–155 页;金和金,引文1972 年,第 153-154 页;金,引文2016年,第。144)。其领导人之一,Chŏng Chongmyŏng(1896-?)脚注3——他的生平和活动将在下面详细介绍,1924年10月,他在朝鲜有声通乌会主办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呼吁与“无产阶级阶级解放运动”合作,不出所料,他被不断警惕的人阻止了。出席的警察(金,引文2016年,第。145;汤加日报,引文1924)。
继恩格斯和倍倍尔之后,一位社会主义女性领导人胡清淑脚注4 (1902-1991),在1924年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纲领性文章(以笔名Sugai《汤加日报》中明确表示女性真正的自由(金,引文2016年,第。146;菅井,引文1924年;另见易,引文2015)。脚注5然而,社会主义妇女领导人经常在公开讲话中提到韩国妇女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Chǒng,引文1933)是他们普遍的“无知”。大多数妇女在殖民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下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Kim,引文2016 年,第 149-156 页)。这种“无知”包括——当然,绝不限于——缺乏有关医学问题的科学信息,包括那些与女性性别角色(性、分娩和抚养孩子)直接相关的问题。对女性中普及医学知识需求的认识是 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的女性社会主义者重视她们队伍中医务人员的作用的背景,例如这一行动的中心人物伊托教(1897-1932)。文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人们对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韩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书籍、书籍章节、脚注6和论文(参见 Cho,引文1990年;帕克,引文1993年;义,引文1992)。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文学成就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参见Kim,引文2011,第 161-191 页),并且最近也对 Kollontai 的思想在日本和韩国的接受情况进行了仔细研究(Pae,引文2018)——就像 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受过激进教育的女性对革命性亲密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一样(Yi,引文2006)。1920 年代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 Chŏng Chongmyŏng 或 Hǒ Chǒngsuk(上文提到了他们的先驱角色),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活动在多篇学术文章中都有详细介绍。脚注7然而,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现代医学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尚未被实质性涵盖,伊托吉的个性也未能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借鉴现有的研究文献语料库(参见 Kim,引文2016年),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特别关注易的女权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承诺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势力的生命政治方面以及更具体的社会医学议程同时冲突和部分重叠的方式殖民政府及其媒体。虽然 20 年代的左翼女权主义和殖民医学代表了现代性计划中相互不同且本质上冲突的方面,但它们之间存在交叉,因为它们都倾向于积极评估现代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取向如何)应该运用的生物权力。这种重叠使易有机会利用殖民地媒体,包括政府运营的媒体,开展对妇女的医学启蒙运动,正如我将试图证明的那样,它们同时带有自己隐含的意识形态议程,最终与殖民当局的意图和目标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只有在 1920 年代日本和韩国对非异性恋亲密关系采取相对自由态度的氛围中,伊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女同性恋过去。最终,在易烊千玺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评价她作为女性主义历史人物的作用和成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伊公开承认自己的女同性恋过去只有在 1920 年代日本和韩国对非异性恋亲密行为相对自由的氛围中才有可能。最终,在易烊千玺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评价她作为女性主义历史人物的作用和成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伊公开承认自己的女同性恋过去只有在 1920 年代日本和韩国对非异性恋亲密行为相对自由的氛围中才有可能。最终,在易烊千玺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评价她作为女性主义历史人物的作用和成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Yi Tǒgyo——学生、医生和活动家
据了解,易是咸兴人——至少早在 1930 年代中期,日本当局的记录中就有她位于咸兴中心地区的地址(Chōsen Sōtokufu,引文1934 年,第 17 页。301)。我们对她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但从她1913年以最好的成绩从当地公立小学毕业后就必须寻找有报酬的工作这一事实来看(Maeil Sinbo,引文1913年),我们可以假设她的出生家庭富裕到足以让她接受小学教育,但又不足以支付继续深造的费用,迫使她寻找工作。尽管如此,伊在小学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顺利毕业,这一事实表明她的家庭一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很可能在意识形态上面向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即 1919 年,韩国学龄女孩上小学的比例也仅为 4%。六年前,这一比例约为 2%,只有 21% 的小学女生完成了学业,其余的都辍学了。缺乏学校、贫困以及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公共教育对女孩来说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引文2009a,第 79-94 页)。在此背景下,可以说,易女士属于极少数,但在 1910 年代(即日本殖民统治的第一个十年)进入公共教育和现代技术就业的女性中,人数极少,但日益引人注目和影响力。朝鲜。
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后,伊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一份工作,那就是在殖民政府将军(Maeil Sinbo,Maeil Sinbo,引文1914a ,引文1914b)。Hamhŭng 的 Chahye 医院由日本护国当局于 1910 年 1 月建立,最初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日本军医 (Ch'oe, K.,引文2016 年,第 59-61 页)。最初,就像它在 Chŏnju 和 Ch'ŏngju(建于 1909 年)的姊妹机构一样,它应该免费“给予”韩国将现代医疗技术带给当地民众,从而赢得了人心,因为该国将于同年 8 月被日本完全吞并。然而,到了 1910 年代中期,Chahye 医院,包括 Hamhŭng 的医院,被迫引入患者费用,因为总政府从未优先考虑的预算进一步减少(Pak,引文2005 年,第 227-261 页)。1910 年,83.4% 的患者在这些医院免费接受治疗,但到 1917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61.9%(Yǒ 等人,引文2018 年,第 17 页。254)。由于合格的护士供不应求(1915年韩国只有215名有执照的护士,其中只有21名朝鲜族,其余大部分是日本人,见Kim,引文2019b,p。87),每家 Chahye 医院将为最多 20 名 17-30 岁的女孩提供为期一年半的内部护理培训(Chŏng,引文2021 年,第 17 页 332)。1913年,李氏满了17岁(按照韩国人的计算,出生时增加了一岁),他是那一年被选中接受护理治疗并在咸兴市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医疗机构之一工作的人之一。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大概已经攒够了继续教育的钱,易于 1918 年继续在东京学习,最终考入著名的东京女子医学院。成立于 1900 年,自 1920 年起有权授予无需单独考试的正式行医执照(Sakai 等人,引文2010年,第。341),它是日本第一家培养女性医务人员的教育机构。其最早的韩国毕业生是著名的胡永淑(1897-1975),也被称为小说家李光洙(1892-1950)的妻子;她于 1917 年完成学业,并于 1919 年获得行医执照(Sin,引文2012 年,第 32-33 页)。她与东京女子医学院的其他八名韩国学生一起参加,他们是在 Yi (Ch'oe, Ŭ.,引文2016年,第。291),是日本朝鲜殖民地的女医生先驱之一。Hŏ 是一位富商的女儿(Sin,引文2012年,第。27) 和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大多数其他韩国学生也来自富裕家庭 (Ch'oe, Ŭ.,引文2016 年,第 291-293 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三位在国内接受培训的韩国女性医疗实践先驱,她们作为例外获准在首尔公立医学院旁听课程,并于 1918 年获得执照,稍早于 Hǒ(Kim,引文2019b,p。68)。金永兴和金海志出身于中产阶级新教皈依者家庭,而安寿京是一位改革派儒家学者的女儿,1909 年之前在政府任职。有趣的是,安寿京的兄弟安光泉 (1897-?)脚注8一位医生出身的社会主义活动家(Yi,引文2021)最终与李亨京结婚,李亨京曾经是李图教的女同性恋情人。
与他们相反,伊托教是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女儿。由于无法依靠父母的支持,她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以极大的决心学习。据她后来的供述,她在东京期间太专注于学业,以至于安全毕业并获得文凭后才去了著名的上野和日比谷公园。过度专注于学习加剧了易的健康问题(Maeil Sinbo,引文1931年),后来她35岁就去世了。尽管如此,尽管她的学业繁忙,易也抽出了时间和精力参加女学生运动——考虑到社会运动在中国的普遍兴起,这并不令人惊讶。继 1919 年 3 月 1 日开始的泛民族支持独立抗议活动的变革性经历之后,1920 年代。从 1921 年 1 月起,李共同负责Yŏja Hakhŭnghoe(妇女教育发展协会)的财务,该协会是一个由韩国女性建立的团体东京的学生。该团体的组织者是Yu Yŏngjun(1892-?),脚注9李易的同学出生于一个较贫穷的平壤家庭,她一度被迫在一所为未来的女艺人(kisaeng)而设的学校学习,并与民族主义者有联系,自 1920 年代中期以来,还与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有联系(Ch 'oe,Ŭ。,引文2016 年,第 292–298 页;黄,引文1933)。后来,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Yu和Yi最终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在韩国本土再次合作。
一名学生活动家,曾经是一名女同性恋(见下文),随后成为朱重根(1895-1936)的情人,后来成为韩国地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关于他的生平,请参阅吉洪诺夫,引文2023),在她的学生时代(我,引文2019年),伊托教于1924年回到庆尚(首尔),一位坚定的“红色”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合格的医生。易首先在总督府中央医院担任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和妇科医生,之后于 1928 年 5 月在 Inch'ǒn 的一个相当偏远的地区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汤加日报,引文1928)。1930 年,她将诊所从 Inch'ǒn 迁至庆尚市中心区(Maeil Sinbo、Maeil Sinbo、引文1931)。从 1927 年到 1931 年,易也属于 Kŭn'uhoe 背后的核心活动家群体,Kŭn'uhoe 是一个“统一战线”妇女运动组织,旨在巩固大多数基督教“新女性”温和派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之间的不稳定合作(Kyōshōkō hi dai)引文第5865章引文1927,第。7). 1927 年 4 月,她加入了成立《Kŭn'uhoe》(汤加日报,引文1927a)。1927 年 5 月,Kŭn'uhoe 刚成立不久,易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有趣的是,与她学生时代亲密的女同性恋前伴侣李贤京 (Tong'a Ilbo,引文1927b)。直到最后,她仍然是一名坚定的库努霍活动家。报纸报道称,1930 年 3 月,她被任命负责起草该组织的庆尚支部(朝鲜日报、引文1930)。
Kŭn'uhoe 和殖民地朝鲜的社会景观
第一个暂时统一左派和右派的泛全国女性团体(与以 Sin'ganhoe 形式建立的泛全国左右联盟并行,1927-1931 年;参见 Yi,引文1993 年,第 17 页。210, 216),韩国和英语学术界的历史学家对 Kŭn'uhoe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韩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开创性专着中有一个关于 Kŭn'uhoe 的专门章节。作者的结论是,到了 1928 年,左派已经逐渐在 Kŭn'uhoe 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像 Hǒ Chǒngsuk 这样的 Kŭn'uhoe 著名左翼领导人的被捕决定性地削弱了该组织(Kim & Kim,引文1973 年,第 72-101 页)。韩国国立韩国历史研究所 ( 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 ) 制作的最新多卷正典版韩国历史强调了 Kŭn'uhoe 意识形态核心的三重重叠,这种意识形态同时是现代主义的(明显是激进的)相对于“封建遗迹”或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模式),反殖民主义,此外,反资本主义( 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引文2001 年,第 298-311 页)。在英语历史学术界,威尔斯强调了库努赫(Kŭn'uhoe)的基督教女性在性别和私人领域政治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她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保持单身,这在一个期望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的社会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个人选择) )并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男性活动家将妇女议程置于所谓“更高级别”国家或社会问题的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比较( Wells,引文1999)。总而言之,现有文献描绘了一幅基督教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议程交叉的女权运动图景,它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反殖民斗争的总体轨迹紧密交织在一起。
然而,最近的社会史开始不仅更加关注库努赫所宣称的理想或其在反殖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方案中的地位,而且还更加关注其领导人和成员的社会背景,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双方。正如韩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金庆日 (Kim Kyŏng'il) 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行动主义,无论是在 Kŭn'uhoe 框架内,还是在 Kŭn'uhoe 之前和之后,都与城市无产阶级或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希望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最终受益者。例如,Chosǒn Yǒsǒng Tong'uhoe韩国女同志协会(Korean Female Comrades Association)是朝鲜社会主义妇女的先锋组织,成立于1924年。截至1925年12月,其73名成员中有学生、护士、教师和家庭主妇,但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截至 1929 年底,Kŭn'uhoe 的会员总数为 2,135 人,但只有 7.7% 的会员是工人或农民;大多数(58.8%)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家庭主妇。从这个角度来看,Kŭn'uhoe的各种教育活动(讲座、夜校等)更多的是少数激进的现代化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一次尝试,目的是接触大多数生活静止的韩国女性,总的来说,嵌入了不同性别角色的遗传模式中(Kim,引文2016 年,第 157-159 页)。
紧随 Kŭn'uhoe 研究的这一新趋势,我想强调通过教育进步实现垂直流动的现代模式在 Yi Tǒgyo 和她的 Kŭn'uhoe 同志的生活轨迹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易烊千玺体现了现代性,即使是在殖民时期,也至少为一些弱势群体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脚注10出生于历来受歧视的朝鲜北部地区脚注尽管她年仅11岁,出身于贫困家庭,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现代学术成就的阶梯,成功地跻身殖民地社会的地理和社会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易烊千玺之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两派的其他一些库努霍活动家也体现了现代发展所带来的急剧向上流动的轨迹。在筹备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妇女中,Yu Yŏngjun(1892-?)脚注12上述与她的学生活动有关的东京女子医学院的一名妇科医生和毕业生,出生于平壤的一个贫困家庭(Maeil Sinbo,引文1922)。Chŏng Ch'ilsŏng(1897-1958)是一位前职业艺人( kisaeng)(关于她的生活和激进活动,请参阅 Pak,引文2019),而Chŏng Chongmyŏng(1896-?),脚注13 岁是一名执业护士和助产士,出生于韩国首都的一个贫困平民家庭(Ch'oe & Sǒn,引文2020 年,第 17 页 147)。
Yi Tŏgyo、Yu Yŏngjun 和 Chŏng Chongmyŏng 通过获得医学和/或托儿所/助产士方面的高级或中级资格,成功地大幅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脚注14 Chŏng Ch'ilsŏng 学习英语、打字。1922 年和 1925 年在日本学习和应用艺术,并凭借其教育资历将自己重塑为社会活动家(Pak、引文2019 年,第 135-136 页)。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她们渴望创造条件的产物,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较贫穷、未受过教育且在国内受压迫的韩国妇女能够按照李氏的路线提高她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 Tŏgyo、Yu Yŏngjun、Chŏng Chongmyŏng 和 Chŏng Ch'ilsŏng 自己的人生道路可能会有所暗示。这些社会主义妇女一定很清楚,在殖民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如此大规模的地位提升是不可想象的,这可能会刺激她们对现代生活的替代形式的追求(Kim,引文2005 年,第 6-7 页)。
在基督教方面,来自贵族(两班)地主家庭的妇女比例较高,但至少 Kŭn'uhoe 的基督教倡导者之一 Kim Hwallan(1899-1970 年)是来自 Inch'ŏn 的仓库老板的女儿来自朝鲜西北部,家境温和。她的母亲——她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在结婚生子之前就有过当丫鬟、当小妾的经历(叶,引文2005年,第。402)。在传教机构接受教育,然后通过传教渠道出国留学,往往可以为有抱负的贫困女性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这些女性因教育的承诺和公共空间的后续进步而被基督教使命所吸引(Choi,引文2009 年,第 86-120 页)。
通常,Kŭn'uhoe 活动家都是向上流动的女性,她们的社会崛起归功于现代教育和职业女性潜在雇主(如医院、教育机构或报纸)的出现。当然,库努赫的议程不仅限于改善妇女的教育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 1929 年的计划既包括法律上完全的性别平等,也包括更激进的、受社会主义启发的要求,例如改善农民妇女的经济状况以及为女工引入强制性的为期两周的带薪产假。除此之外,Kŭn'uhoe 希望消除工资方面的性别歧视,废除妇女和儿童的危险劳动和夜班以及殖民警察事实上纵容的贩卖女性行为脚注15(朝鲜日报,引文1929;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引文2001,第 306–307 页)然而,Kŭn'uhoe 的女性专业人士体现了通过教育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殖民现代性至少向一些韩国妇女开放,并致力于在韩国女性人口中传播现代知识,Kŭn'uhoe尽管有明显的激进主义,但它可以与殖民当局共存——尽管相当不稳定——毕竟,殖民当局的合法性是基于他们(相当牵强的)声称要实现“落后”韩国的现代化。1920 年代日本殖民地的“文化政策”,旨在通过受控组织,让殖民地新兴的中产阶级至少获得某种程度的半独立,以确保他们的长期合作(Robinson,引文1988 年,第 48-51 页),是 Kŭn'uhoe 型激进主义与殖民秩序之间不稳定共存的另一个背景。
医学知识普及与殖民生命政治
当 Kŭn'uhoe 忙于在韩国女性中传播现代知识时 (Kuksa p'yŏnch'an wiwŏnhoe,引文2001,第307-308页),特别是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是易确实擅长的活动领域。作为一名受欢迎的医生,易作为报纸和期刊的医学问题撰稿人而广受追捧,为她的大部分女性读者提供从百日咳到子宫内膜炎等各种疾病的建议。她作为殖民时代韩国女性医学知识的主要普及者的角色仍然有待研究人员的适当关注。
易氏以妇女为导向的医学知识普及运动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强调疫苗接种(易氏,引文1927c)和预防,特别是卫生方面。例如,在谈到百日咳时,易强调了它的细菌性质及其通过已感染人类的咳嗽传播,并要求她的读者尽最大努力隔离那些已经患病的人,以防止进一步传染(易,引文1930b)。理想情况下,她希望韩国家庭专门设立一个单独的隔离房间来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并确保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彻底隔离(Yi,引文1930a)。关于子宫内膜炎这一敏感话题,易将女性丈夫的淋病感染列为各种盆腔炎的主要原因,并建议女性在结婚前向未来的结婚对象索要健康证明(易,引文1930c)。还劝告女性读者劝说她们的丈夫在经期避免任何性接触,以防止任何传染的可能性(Yi,引文1930c)并提醒女性盆腔炎症可能会阻碍她们怀孕(Yi,引文1930c)。除此之外,与她同龄的许多其他医学专业人士一样,易相信女性自慰会增加神经衰弱和慢性头痛的危险(Yi,引文1930e)。与主流(男性)医疗专业人士类似,易将性传播疾病首先视为一种潜在的生殖危险,同时强调先天性梅毒可能给受感染妇女的孩子带来个体痛苦,其中包括失明和骨骼畸形等。主要危险。她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丈夫对性交卫生方面的责任;这与 1920-1930 年代更保守的男性医疗专业人员通常强调女性的性卫生责任形成鲜明对比(Yi,引文1930d)。脚注16总而言之,虽然易的医学建议试图向她的读者传达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被认为是科学医学真理的相当标准的版本,但她强调妇女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以及丈夫对其女性伴侣的责任健康和安全,以及成功预防措施的社会先决条件(为患者提供单独的房间等)揭示了她议程中的社会进步和性别解放方面。
与易的医学普及活动相关的一个有趣的观察是,特别注意哪些报纸刊登了她关于一般和女性特定健康问题的大量文章。当然,其中一些文章发表在韩国经营的日报《东亚日报》上,该报往往为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的激进知识分子提供论坛。不过,其他文章则由日本政府日报《每日新报》刊登- 将军的喉舌。有趣的是,易烊千玺与每日新播的关系甚至早于她获得医生身份之前。早在1913年秋天,总督府的官方文件就称赞这位未来的“红色女权主义者”是“模范妇女”,称赞她既以最好的成绩从当地小学毕业,又是学校里“最有礼貌的护士”。当地医院,从而赢得了患者的感谢(Maeil Sinbo,引文1913)。第二年,同一篇论文中出现了更多的赞扬,更多的患者向这位“温顺、人道、行为良好、善良”的护士致敬,重要的是,她拥有出色的日语能力(Maeil Sinbo,引文1914a ,引文1914b)。在前往东京学习之前,易在咸兴工作的医院是一家政府医院;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回到韩国后,易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韩国首都的一家政府综合医院。日本警方文件表明,从大约 1927 年起,易就作为共产主义活动家受到监视(Chōsen Sōtokufu,引文1934 年,第 17 页。301)。然而,这并没有浇灭Maeil Sinbo发表医疗建议的热情。有趣的是,易并不是唯一一位《每日新播》准备发表医疗建议的 Kŭn'uhoe 成员。Chŏng Chayŏng(1896-1970)是东京女子医学院的另一位毕业生,曾经活跃在Kŭn'uhoe,她也有幸在殖民当局的官方报纸上发表对韩国妇女的劝告。例如,她认为历史悠久的暖炕地板采暖系统使韩国房屋比西方房屋更不“卫生”,并对韩国家庭缺乏正规的体育活动表示遗憾(Chŏng、引文1926)。到 1930 年,她已经开始批评韩国人所谓的“非理性”以及他们对“一切新事物”的假定偏好(Chŏng,引文1930年;另见 Ch'oe, Ŭ.,引文2016年,第。309)。
殖民地政府和拥有医师执照的反殖民女性激进分子之间持续不断的专业互动表明,尽管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殖民地的激进医生和帝国主义统治者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如上所述,殖民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主张在其殖民地领域实现现代化“改革和改进”的主张(本质上是自私且极其值得怀疑的),它是生命政治的积极实践者。脚注17它管理着一些医疗机构,在明确将现代国家权力的纪律、团方面的方面置于医疗机构之上的同时,还实行疾病预防和控制政策,以至于相关机构的(高度有限的)预算会允许的。事实上,报纸上发表的医疗建议是最便宜的预防措施。除了公民道德教科书、公开讲座、甚至 20 年代末的广播中的卫生建议外,它还被广泛使用(Hwang,引文2016 年,第 239-242 页)。因此,即使是一位知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也被允许向总督自己的报纸发表一些有关医疗问题的有用文章,这可能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反过来,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也将医学视为他们解放另类现代性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免费医疗——苏联国家公开的目标,朝鲜共产党在 1920 年代的模式(到 1937 年全面引入苏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计划中所希望的革命的公开目标之一1920 年代(参见 Tikhonov 和 Lim,引文2017)。毫不奇怪,当大众健康知识问题受到威胁时,易代表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并不认为与殖民政府合作是令人反感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模式
然而,与此同时,易也作为一名积极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被日本警方理解为(如上所述)朝鲜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女权激进分子,她希望女性在社会经济和亲密关系领域都获得赋权。她认为与劳工运动的紧密联盟——但不是归结于劳工运动——是有效改善贫困职业妇女社会经济状况的唯一希望。然而,她的女权主义不仅仅是她激进政治承诺的延伸。她被认为是妇女提起离婚诉讼的道德权利的坚定倡导者。这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婚姻仍然是包办的,而且结婚双方本身的同意往往是纯粹正式的(Yi,引文1927b)。与此同时,她在期刊、讲座和圆桌讨论中的许多文章中做出了值得注意的尝试,概述了她对解放性亲密关系的愿景。例如,她认为男性的专横、霸道态度是当代韩国婚姻不和谐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朝鲜日报》,引文1927)。与大多数同时代人(男女)一样,易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就不同,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灵活和坚定”。然而,她同时相信女性还有其他优势,并且拒绝认为两种性别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天生优越的”(易,引文1929)。
其中许多文章也揭示了易本人与汉·维根的婚姻生活脚注18(1896-1937),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之一,也是《汤加日报》的,该报在 1927-1930 年间发表了易的一些文章。易非常欣赏她和丈夫之间存在的“理解”(易,引文1928)。她的经历告诉她,“充分理解”,即婚姻中相互鼓励、平等和支持的同志关系,是对抗焦虑和恐惧的有效解药,否则这些焦虑和恐惧是激进活动分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Yi,引文1927a)。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伊对与韩的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导致她跟随他流亡到中国,并最终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去世。
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和她在Kŭn'uhoe(殖民地庆尚解放妇女的代表)的许多同事都对女性同性恋表现出了非常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910-30年代并不罕见,因为各种女性同性恋亲密行为经常伴随着女学生相对僻静的宿舍生活脚注19名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人(Pak-Ch'a、引文2018 年,第 231-236 页)。然而,这听起来仍然对主流社会构成挑战,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易。例如,她很乐意分享她在日本学生时代的女同性恋爱情经历的记忆,这显然早于她与楚重官的异性恋关系(易,引文1930f)。她的情人是李亨京(1902-?),脚注20出身于水原(京畿道)富家子弟,当时是东京女子大学的学生,先是基督教运动,后又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后来,一位社会主义 Kŭn'uhoe 活动家 Yi Hyŏn'gyŏng 最终嫁给了 An Kwangch'ŏn(1897-?),脚注21一位医生出身的共产主义活动家(Cho,引文2010,第 273-274 页),她与丈夫于 1929 年左右逃往中国(Kaebyŏk,引文1935)。Yi Tǒgyo 和 Yi Hyŏn'gyŏng 显然都是双性恋,并且似乎认为她们的女同性恋事件是很自然的,符合她们的学生身份(对于大多数女大学生来说,成为学生实际上阻止了结婚和随后的生育)。Yi Tǒgyo 与她的读者分享了她与 Yi Hyŏn'gyŏng(“一直睡在一条毯子下”)的强烈肉体关系,以及她的多角恋倾向(她同时追求几段平行的女同性恋爱情,其中一场与一个种族日本同学)以及她对开放关系的偏爱导致她嫉妒的伴侣(据报道他曾经接近自杀)遭受了极度的心理痛苦(Yi,引文1930f)。伊托教对爱情的态度似乎很可能受到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关于非专有恋爱关系的理论的影响,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该理论在左翼女权主义者中具有很大影响力20 世纪 20 年代的日本和韩国。
柯伦泰的理论在她所处的时代和后来经常被曲解为提倡滥交,或者至少提倡与多个伴侣建立开放的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也不是 20 年代韩国女性激进分子(包括伊图教)解释“柯隆泰主义”的唯一方式。尽管她主要主张轻松离婚,并且相信开放式关系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在她的丈夫于 1927 年将她留在韩国并于 1931 年 5 月因警察迫害领导人而流亡中国后,她拒绝发起任何婚外情。在韩国是共产党员,也是出于她希望与丈夫在一起,维持他们的关系的愿望。
在 1930 年的一篇日记中,易强调,尽管她未满足的性冲动带来了种种挑战,但在丈夫不在的三年里,她仍设法保持对丈夫的忠诚。她始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她补充说,她作为一名合格医生、收入稳定的社会地位很有帮助——她经济独立,不需要因为金钱原因而建立新的关系。虽然她承认,那些在爱人被监禁或流放时完全无法忍受性冲动的女性不应因在等待原来的伴侣回来时开始一段新的关系而受到道德谴责,但她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忠诚对于缺席的伴侣来说在身体上并非不可能,引文1930克)。最后,一种牢固植根于平等主义思想、同志情谊、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似乎是易个人更喜欢的亲密关系模式。非专有态度是实践这种亲密形式的重要先决条件。
易烊千玺飞往北平(今天的北京)是她亲密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据报道,她想和丈夫住在一起,但同时也想在中国的旧首都“工作”,大概是共产主义网络的一部分。日本警方设法找到了她在北平的地址,甚至在那里,在她自己选择的中国流亡地(Chōsen Sōtokufu,引文1934 年,第 17 页。301)。但不久她就病倒在北平去世了。1932 年秋天,这个悲伤的消息传遍了韩国(Kwansangja,引文1932)。最终,伊在中国的流亡生活仅一年多一点,又因一场不治之症,英年早逝。
结论
本文考察了易的生命历程和她的活动,包括职业和社会政治活动。用于分析易的生活和作品的方法包括社会史的方法,特别关注现代教育制度在易的职业生涯向上流动轨迹中的作用,以及在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对她的作品进行批判性的女权主义解读。殖民出版社。殖民地媒体以及日本警方的文件提供了本文中使用的有关易的生活和活动的大部分信息。文章的焦点之一是易烊千玺面对殖民现代性的谈判策略。殖民主义国家权力机构运营的现代教育体系和新闻媒体对于伊的向上社会流动轨迹以及她向韩国女性同胞传播医学知识的运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易因参与激进的反殖民活动而不断受到警方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权宜之计是确定一个她自己所偏爱的(社会主义和解放的)现代性愿景不会与殖民政府的现代化主张发生冲突的领域,即医学知识普及领域,并以女性读者为目标观众。
在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与她参与 Kŭn'uhoe(一个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主要是像易本人一样向上流动的女性专业人士)的泛全国妇女团体 Kŭn'uhoe 的同时),她也非常活跃地作为一个普及者利用所有可用的媒体渠道,包括总督自己的喉舌,传播医学知识。她的医学著作值得在当代女性流行医学建议的背景下重读。与男性医学专业人士相比,易的题材选择和重点强调,微妙地表明了她态度的激进主义。更一般地说,殖民时代韩国的流行医学话语(一些主要材料最近在Ch'ǒngam Taehakkyyo Chaeil K'orian Yǒn'guso中重印),引文2022)未来应该由研究人员重新审视,因为其中许多一旦从互文的角度进行审视,就会揭示出它们与韩国知识分子(和日本知识分子)对性别、家庭、亲密关系以及一些流行的生物政治领域的态度之间的联系。殖民时期的韩国医疗专业人员)。
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公民社会官方允许的领域中,她作为一名医学专家、普及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合法”存在平行于她作为汉族的妻子和亲密战友的第二次生命。维冈(Wigǒn),一位致力于推翻殖民秩序的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双性恋者,伊从未否认自己的同性恋过去。然而,与此同时,她和韩成功地体现了基于拒绝专有态度的异性婚姻伙伴关系的典范,体现了平等、相互理解、同志情谊和信任。他们的“红色爱情”实践对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在韩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地方)激烈的非传统和激进亲密形式的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殖民时代的激进分子在亲密关系中挑战前现代和现代形式的父权制的尝试是超前的。它们可以为废除父权形式的性别关系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参考。脚注22即使在今天的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