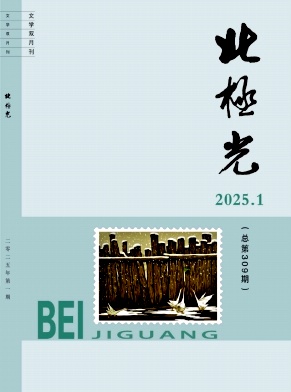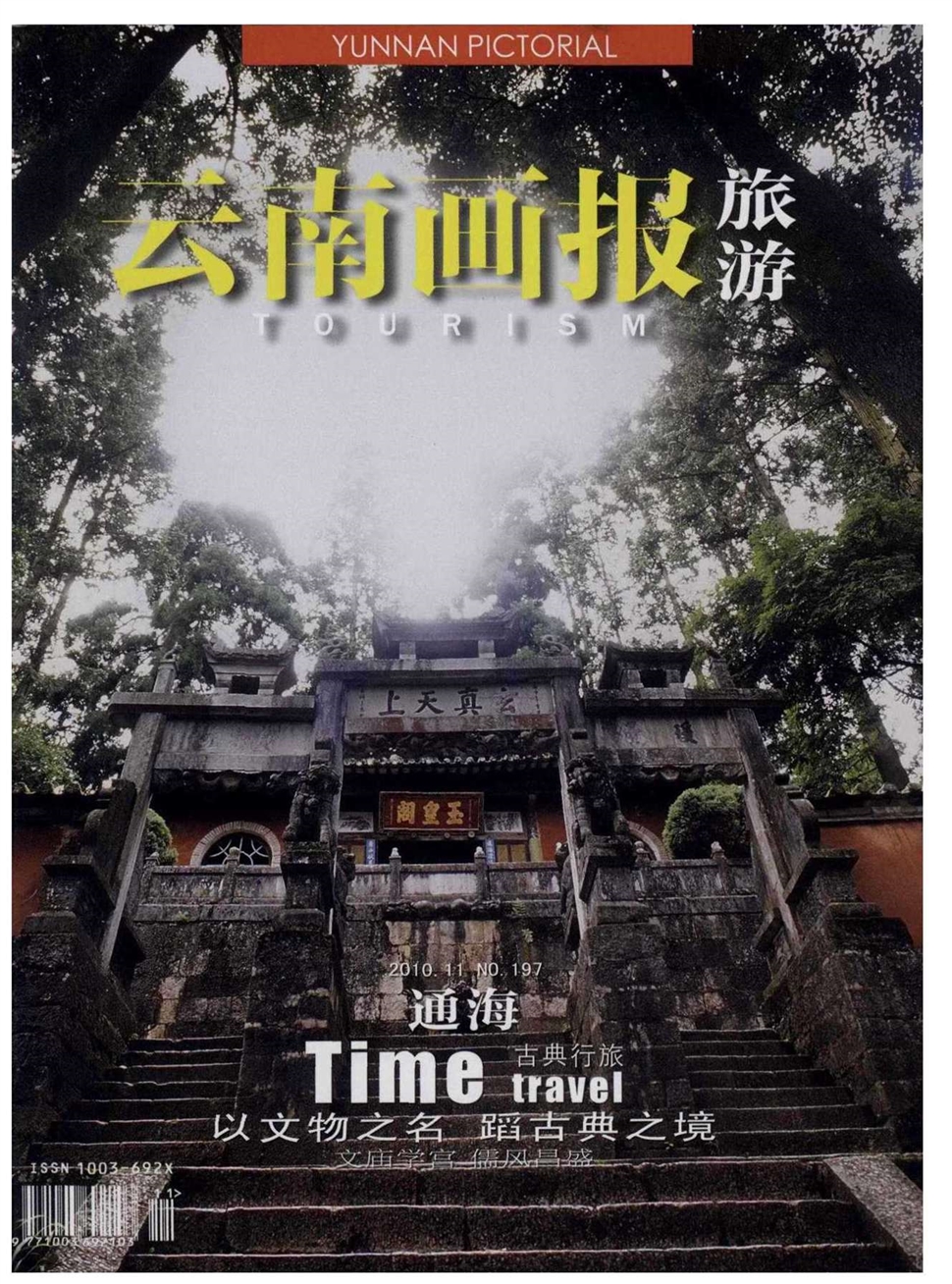新闻资讯
介绍
近年来,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的速度放缓甚至停滞(England等,2015)。 引文2020)。由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了解造成性别工资差距的过程对于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和消除性别工资不平等至关重要。学者们已经确定了造成职业层面性别工资差距的多种因素,例如种族隔离(Grönlund 和 Magnusson)引文2016),以及个人层面,例如人力资本(Blau 和 Kahn)引文2017)。最近的奖学金表明,企业脚注1和工作,即企业内部的职业,对于理解工资分层比职业或个人属性更重要(Avent-Holt等人,2016)。 引文2020 年;彭纳等人。 引文2023 年),这符合 Baron 和 Bielby 的“让公司重新回归”的呼吁(Baron 和 Bielby引文1980)。
在这一呼吁之后,研究人员最近调查了导致公司层面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因素,例如种族隔离(例如 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2),组织实践(van der Lippe、van Breeschoten 和 van Hek引文2019年;齐默尔曼和科里雄引文2023 年),以及女性经理(例如 Van Hek 和 Van Der Lippe)引文2019年;齐默尔曼引文2022)。最近的理论发展也强调了组织对于创造和维持不平等的重要性,例如关系不平等理论(RIT)(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
根据 RIT 的说法,关系主张是通过社会关系在工作场所造成不平等的重要机制(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 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结合群体之间的地位等级(例如 Ridgeway引文2014),分类区别(例如基于性别或国籍)可以使对组织资源的主张合法化,例如薪酬或晋升(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就性别而言,男性和女性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试图帮助同性同事索取组织资源。如果男性在工作场所处于较高的地位类别,那么男性更愿意与其他男性共享资源,可能会通过两种机制导致对女性的剥削:(i) 机会囤积和 (ii) 剥削,从而造成群体之间的不平等(Avent-Holt)和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引文2010年;蒂莉引文1998)。
首先,关于机会囤积,男性可能更愿意将高薪公司的职位或高薪工作的机会让给其他男性,从而导致女性无法获得这些机会。由此产生的收入不同的公司或工作岗位的隔离造成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其次,关于剥削,男性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权力来帮助其他男性比女性更有效地争取工作机会。男性利用关系权力优势,将组织资源不成比例地分配给其他男性,从而造成不平等。这种剥削以牺牲女性工资为代价来提高男性工资(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2)。
在这项研究中,我使用 RIT 框架调查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首先,我通过调查劳动力市场层面、公司层面和工作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差异来测试机会囤积。这些差距之间的差异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低薪公司工作的比例是否过高,以及女性是否在公司内部从事低薪工作。这种对低薪公司或工作的隔离可能是机会囤积的结果。通过调查这两个层面的机会囤积,我可以调查哪个层面的隔离导致了男女工资不平等。
其次,我研究了剥削机制,即男人利用关系权力在主张中获得优势。由于组织资源稀缺,地位较高的团体成员可以帮助下属争取工作机会。高地位群体成员与低地位群体成员的比例可以代表关系权力,因为高地位群体成员可以帮助低地位成员提出主张(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0年;新安怡-霍尔特和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引文2012)。与最近关注女性管理者存在的文献(例如 Zimmermann引文2022),RIT 将重点转移到与组织内部类别区别相关的群体的关系权力上。脚注2关注 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 (引文2010),我使用管理者中女性比例与工人(即非管理工人)中女性比例之间的差异作为女性关系权力的指标。此外,通过考虑工作层面的机会囤积,我可以提取剥削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扣除公司内不同职业的分类)。
第三,我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明确考虑了从男性到女性的工资再分配。先前的文献主要关注女性管理者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例如 Abendroth等人,2014)。 引文2017年;范赫克和范德利普引文2019),理论上没有考虑对男性工资的潜在影响。RIT框架凸显了组织资源的稀缺性。女性工资的下降伴随着男性工资通过剥削而增加,因为给予男性更多的组织资源导致给予女性的组织资源减少(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因此,减少剥削应该通过提高女性工资和降低男性工资来实现男性和女性工资的趋同。我可以通过直接分析潜在的工资再分配来测试剥削机制的双方。
为了研究我的研究问题,我使用了来自德国的纵向链接雇主-雇员面板数据集,即链接雇主-雇员数据 (LIAB QM2 9319)(Ruf等人,2017)。 引文就业研究所 (IAB) 的2021b )。脚注3这个独特的数据集包含 2.632 家私营企业和 1,252,125 名工人观察数据,包含有关公司的丰富组织层面信息,例如有关经理、集体协议的信息以及高质量行政工人数据(例如工资和职业)。
我至少以两种方式对文学做出贡献。首先,通过调查工作层面的剥削,我可以提取隔离剥削网的影响。其次,据我所知,我提供了关于剥削机制再分配方面的第一个证据。由于大多数先前关于 RIT 调查性别或移民工资不平等的奖学金都是跨部门的(例如 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2年;梅尔泽等人。 引文2018年;彼得斯和梅尔泽引文2022),企业内工资对男性或当地人的影响无法估计。纵向数据使我能够调查企业内男性的工资是否受到女性相对议价能力的影响。由于剥削造成的工资不平等是基于群体之间的再分配,因此检查工资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对于彻底调查这一机制至关重要。
关系不平等理论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组织在产生和维持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阿克引文2006年;巴伦和比尔比引文1980年;蒂莉引文1998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在 RIT 框架中,关系主张是产生不平等的核心机制(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关系主张通过工作场所内的社会关系进行运作(彼得斯和梅尔泽)引文2022 年):工人对工作场所资源提出要求,例如工资。雇主判断这些主张的合法性,然后批准或驳回这些主张(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 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虽然能力或生产力可能会增加这些主张的合法性,但 RIT 强调分类区别与基于这些区别的地位层次结构相结合的作用,以用于声明过程(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属于一个具有较高地位的群体可以使对组织资源的要求合法化,而不管实际能力或生产力如何(彼得斯和梅尔泽)引文2022 年;里奇韦引文2014年;蒂莉引文1998)。
机构、组织和个人背景的交叉可能会突出或削弱类别差异(Melzer等人,2017)。 引文2018)。由于本地地位层次结构和互动规范是在组织内部制定的(DiTomaso等人,2017)。 引文2007),当地组织环境影响分类过程,导致群体间的差异(Melzer等,2007)。 引文2018)。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上进行分类和区分的基本且显着的属性(英格兰引文2010年;新安怡-霍尔特和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引文2012)。总之,当地的组织环境导致组织之间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的不平等制度(Acker引文2006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
机会囤积
以马克思为基础(引文1867),韦伯(引文1947 [1924])和蒂莉(引文1998),除其他外,RIT 提供了两种潜在的机制,用于说明类别区别与基于这些区别的地位等级相结合如何导致群体之间的不平等(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首先,群体内成员可能更愿意与其他群体内成员分享进入高薪公司或工作的机会,从而导致群体外成员被排除在这些公司和工作之外。脚注4这种机会囤积导致了工作场所的隔离。其次,更强大的参与者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向群体内成员授予组织资源。这种剥削会导致不平等,而牺牲权力较小的行为者的利益(蒂莉引文1998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
在性别工资不平等的背景下,男性可能更愿意与其他男性分享加入高薪公司或从事高薪工作的机会,从而阻止女性进入高薪工作或公司。有组织的社交封闭(Reskin引文1988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引文1993)以及自我选择不同的工作或公司(Card et al. 引文2016年;里奇韦引文1997)可以促进机会囤积(Tilly引文1998年;新安怡-霍尔特和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引文2012)。如果男性和女性分别从事不同薪酬的工作和公司,公司或工作层面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可能会较低,而国家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可能会很高。因此,为了测试机会囤积,我调查了国家层面、公司内部和工作岗位内的性别工资差距。这些水平之间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差异可能表明女性被隔离到薪酬较低的公司或工作中,从而得出以下假设:
当企业层面的隔离更加普遍时,企业内部的性别工资差距比总体性别工资差距更窄(假设1a)。
当工作层面的隔离更加普遍时,工作内性别工资差距比整体性别工资差距更窄(假设1b)。
开发
虽然机会囤积假设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从事相同的工作,获得相似的工资,但剥削机制可能会导致从事相同工作的群体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从马克思概括(引文1867),剥削被定义为行为者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侵占价值(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2年;蒂莉引文1998)。地位较高的团体内成员可以帮助其他团体内成员提出工作机会的要求,例如工资(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因此,相对地位构成,即群体内高地位成员与低地位成员的比率,代表了行动者的关系权力(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关系权力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组织内群体成员的等级地位。由于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关系权力可以通过公司中管理和非管理工作中群体的相对代表性之间的差异来表示(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0)。
在性别工资不平等的背景下,男性管理者可能会将稀缺的组织资源不成比例地分配给男性非管理员工。这种剥削以牺牲女性工资为代价来提高男性工资,从而导致性别工资不平等(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2)。由于更多的女性经理或更少的女性非管理员工都会增加女性的关系权力,因此我预计女性经理相对于女性员工比例的增加会增加女性的工资,从而得出假设 2a。
女性关系权力的增加会增加女性在公司和工作中的工资(假设 2a)。
根据剥削机制,男性的高工资是由于将稀缺的组织资源不成比例地分配给男性而牺牲了女性的利益(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因此,女性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工资的增加应该伴随着男性工资的下降。由于组织资源稀缺,组织资源在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对于剥削机制至关重要(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这种重新分配导致了假设 2b。
女性关系权力的增加降低了男性在公司和工作中的工资(假设 2b)。
关系权力可能对不同级别的工作资格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德国,教育资格和工作分类紧密相连(DiPrete 和 McManus)引文1996)。因此,学历较低的员工通常从事资质较差、工资较低的工作。雇主对低素质女工工资上涨的抵制可能较小,因为该群体的工资上涨对雇主来说成本较低(Abendroth等人,2017)。 引文2017)。德国先前的研究(Abendroth等人,2017) 引文2017年;齐默尔曼引文2022)表明,特别是低素质的女性工人受益于女性管理人员的存在。每个资格级别的不同影响导致以下假设:
女性关系权力的增加,使没有大学学位的低素质女性在企业和工作岗位上的工资增长幅度高于拥有大学学位的高素质女性(假设2c)。
低素质工人比高素质工人拥有更少的关系权力(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并且可以更容易地更换。因此,低素质男性工人的工资可能会得到更强有力的重新分配,因为高素质男性工人可能会更有效地防止工资下降。先前的研究主要指出从关系权力较小的员工到关系权力较多的员工的重新分配(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例如从较低级别到较高级别的工人(Liu等人,2019)。 引文2010)或从不合格到更合格的工人(Sakamoto 和 Kim)引文2010)。这些考虑引出了以下假设:
女性关系权力的增加,对没有大学学位的低素质男性在企业和工作中的工资的降低作用强于具有大学学位的高素质男性(假设2d)。
德国的制度设置
公司嵌入国家制度环境中,这可能会限制管理人员将组织资源分配给不同群体的自由裁量权(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0)。例如,私营部门的工资主要由个人层面或工作场所层面的谈判决定(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与私营部门可协商的工资相比,公共部门的工资标准集中化、正规化,主要取决于资历(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因此,我重点关注私营企业,以确定女性关系权力在个人和工作场所层面谈判中的作用。
在私营部门,企业也可能签订集体工资协议,规定工作岗位的工资,并防止群体之间任意设定工资(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德国的另一个制度特征是劳资委员会的盛行,这增加了工人,特别是弱势工人的议价能力。集体协议和劳资委员会应该减少性别工资不平等,因为它们减少了企业剥削的机会。我认为德国的关系权力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大,因为 2020 年德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欧洲排名第五(欧盟统计局引文2022)。
数据和测量
数据
为了检验我的假设,我使用了德国纵向关联的雇主-雇员数据 (LIAB QM2 9319)(Ruf等人,2017)。 引文2021b ,引文2021a;乌姆凯勒引文2017)由就业研究所(IAB)提供。该代表性数据集包含每年调查的公司层面有关就业相关主题的信息,例如管理层组成、集体协议和工作委员会(Ruf等人,2017)。 引文2021a)。LIAB QM2 9319 是从德国所有公司中抽取的分层随机样本,截至上一年 6 月 30 日,这些公司至少雇用一名须缴纳社会保障的员工(Ruf等人,2017)。 引文2021a)。面对面访谈主要由专业访谈员进行。由于大多数受访者从事管理工作,因此可以假设数据质量很高。
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因为这些年可以获得有关管理层构成的信息。脚注5我将公司层面的调查数据合并到受调查公司工作的所有缴纳社会保障的员工的行政就业记录中。我关注的是至少拥有 10 名员工的私营企业,并且在每个调查年份至少雇佣一名年龄在 20 岁至 60 岁之间的全职男性和女性员工。我根据职业规范排除了经理,以避免经理的工资使我的结果产生偏差,因为这些假设是针对非管理员工级别的。此外,我关注全职工人,因为数据缺乏有关确切工作时间的信息。最后,我排除了控制变量部分概述的变量之一中缺少信息的公司。在这些限制之后,我的平衡面板样本包括 2,638 家公司、475,427 名独立全职工人以及 1,252 名
测量
工资
我的因变量是工人的日总工资(欧元),该工资来自社会保障缴款,并缩减至 2015 年。与基于调查的数据相比,此信息不会出现误报或选择性不答复的情况(Avent-Holt等人。 引文2020 年;代客泊车等人。 引文2019)。由于工资信息是根据法定养老保险的收入上限进行审查的,因此我使用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按性别、地区(东德和西德的位置)和日历年分别估算紧缩工资(Stüber et al.,2017)。 引文2023)。为了消除随机生成的异常值,我将估算工资审查为第 99 个百分位数的十倍(每天 757.53 欧元)。
工作
有关职业的详细信息对于确定工作至关重要。遵循文献(Avent-Holt等。 引文2020 年;彭纳等人。 引文2023),我用3位职业代码区分了140个职业,实现了岗位的细粒度识别。使用有关职业的行政信息可以规避调查数据的问题(Avent-Holt等,2017)。 引文2020),即报告和编码错误(Speer引文2016)。作为稳健性检查,我还使用 4 位职业代码来区分 540 种职业(Ruf等人,2017)。 引文2021a)。
女性关系权力
公司中女性的关系权力由公司的相对性别构成来代表,即管理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与非管理人员中全职女性比例之间的差异(Avent-Holt 和 Tomaskovic-Devey)引文2010)。
Femalerelationalpower=Femaleshareofmanagers−fulltime-equivalentfemaleshareofnon-managerialworkers
有关管理人员中女性比例的信息是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因为行政数据不包括无需缴纳社会保障缴款的管理人员,例如公司的高管和所有者(Zimmermann引文2022)。调查数据将管理层分为两个层级:高管和主管。我通过将所有管理级别中的女性管理人员数量除以所有管理级别中的管理人员数量来计算女性管理人员比例。我计算了职业代码未表明管理职业的公司中所有有社会保障义务的工人中非管理工人的全职等效女性比例。由于无法获得确切的工作时间信息,我将全职工人设为 1,将兼职工人设为 0.5。参见附录图 A1,了解公司中女性关系权力的分布。作为稳健性检查,我还按管理层单独计算了关系权力。
控制变量
遵循使用 RIT 调查德国工资不平等的文献(Melzer等,2017)。 引文2018年;阿本德罗斯等人。 引文2017),我控制了个人层面的人口和人力资本变量,即以年为单位的年龄、其平方、教育的三个虚拟变量、以年为单位的任期以及以年为单位的劳动力市场经验。我在模型中考虑了职业层面的 140 种职业,没有职业固定效应。在公司层面,我考虑了公司固定效应,它控制了所有时间恒定的公司层面变量(Abendroth等人,2017)。 引文2017)。对于公司层面的时变变量,我考虑员工的对数;公司自我报告的利润评估;全职等值股份脚注高素质工人(即具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女工人、定期工人6人;兼职工人的比例;是否存在劳资委员会;公司层面和部门层面的集体协议(Zimmermann引文2022)。考虑到德国的制度环境,我还控制了女性和集体协议的相互作用以及工作委员会的存在,因为这些变量理论上会影响性别工资不平等(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最后,我控制了观察年份的虚拟人。有关这些变量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附录表 A1;有关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请参阅附录表 A2。
分析策略
为了估计性别工资不平等、隔离和女性在公司内的关系权力之间的关系,我采用了在公司层面和工作层面具有固定效应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Wooldridge)引文2010)。由于该理论侧重于组织内部的流程,因此我的估计是公司中女性关系权力与公司内部或工作内部性别工资差距之间的关联(Lundberg等,2016)。 引文2021)。固定效应模型相当于也经常使用的分层线性模型,只是在公司或工作层面使用固定效应而不是随机效应(Melzer等,2017)。 引文2018)。公司和工作固定效应考虑了公司或工作之间未观察到的时间常数差异(Rabe-Hesketh 和 Skrondal)引文2012),例如工业部门。女性系数代表样本均值的性别工资差距,因为在与未贬低的女性虚拟变量(Imbens 和 Wooldridge)进行交互之前,我贬低了关系权力、工作委员会和集体协议等变量引文2009)。
为了估计公司和工作隔离的影响,我首先估计没有控制变量的模型(1)来估计原始性别工资差距。我添加了逐步的个人层面控制变量(模型(2))、职业层面固定效应(模型(3))、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和公司固定效应(模型(4)),最后是工作层面固定效应(模型(5))来估计劳动力市场不同阶段的性别工资不平等。例如,添加企业固定效应来控制企业内的平均工资水平,即对不同薪酬的企业进行分类。因此,当加入公司固定效应后性别工资差距缩小时,结果表明女性在工资较低的公司工作。使用这种常用策略来识别隔离的影响(例如 Peters 和 Melzer引文2022 年;梅尔泽等人。引文2018),我可以检验假设 1a 和 1b,即女性被隔离到薪酬较低的公司和工作中。
模型(4)和(5)还包括我的兴趣变量、公司中的女性关系权力及其与女性的互动。在这些模型中,我检验了假设 2a 和 2b,即增加女性关系权力是否会增加女性的工资并降低男性的工资。由于该理论假设公司或工作中的群体之间存在重新分配,因此我使用包括公司或工作固定效应的模型来分析假设 2a 和 2b。为了提供假设 2c 和 2d 的证据,我将样本分为低素质工人(即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和高素质工人(即具有大学学位的工人)。为了计算这些效应的差异并研究假设 2c 和 2d,我估计了一个三向交互模型。
在主要结果的模型(4)和(5)以及检验假设2c和2d的回归中,女性关系权力的主效应代表了女性关系权力与男性工资之间的关联。该系数与女性的交互作用代表了男女系数的差异,即与工人性别工资差距的关联。平均边际效应是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总和,代表了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资之间的总关联。
结果
为了衡量机会囤积,我用不同的控制变量计算了性别工资差距。首先,我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计算原始性别工资差距。第 1 栏表格1显示我的样本的原始性别工资差距为 19.9% (exp(−0.222)−1),高于德国 2020 年未经调整的性别工资差距 18.3%(欧盟统计局引文2022)。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对全职就业和私营部门的关注来解释,因为德国全职雇员的性别工资差距更大,而私营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更大(欧盟统计局引文2022)。接下来,我通过添加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即工作经验、任期和教育程度)来计算调整后的性别工资差距。调整后的性别工资差距为 15.3% (exp(−0.167)−1),比未调整的差距小 23.1%脚注7(第 2 列表格1)。原始性别工资差距和调整后性别工资差距之间的差异可以归因于个体差异。在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小幅收窄至 14.6%(exp(−0.158)−1),比调整后的性别工资差距小 4.6%(第 3 列)表格1)。
在企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至 10.2% (exp(−0.108)−1),比职业内部调整后的性别工资差距小 30.1%(第 4 列)表格1)。分成不同的支付公司可以解释这两个差距之间的差异。由于女性平均进入工资低于男性的企业,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比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异更大。我的结果证明了假设 1a,即女性在薪酬较低的公司工作的平均水平低于男性。这种隔离可能是机会囤积的结果。
在工作岗位内,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至 8.7% (exp(−0.091)−1)(第 5 列表格1)。这一差距比企业内部的差距小 14.7%。由于工作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低于公司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因此我的研究结果暗示了工作层面的隔离,即在同一家公司中,女性从事的工作薪水低于男性。公司内部的这种隔离进一步表明了机会囤积和假设 1b,即女性平均从事比男性工资更低的工作。总之,从公司或工作内部来看,性别工资差距大幅缩小,因为工作中的差距比原始差距小了 56.3%。我的结果显示公司和工作层面存在隔离,表明存在机会囤积现象。
尽管分入不同的公司和工作岗位解释了性别工资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但即使在工作层面,男性和女性之间仍然存在显着的工资差异。第二种机制,即通过关系权力进行剥削,可能可以解释这些剩余的差异。第 1 列和第 2 列表2研究表明,较高的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资上涨有关。该系数在公司内部规模(第 1 列)和内部工作规模(第 2 列)方面非常相似。这一结果是假设 2a 和剥削机制的证据,因为即使从事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关系权力也与女性的工资相关。对于男性,第 1 列和第 2 列表2两种回归模型都显示女性较高的议价能力与男性工资之间呈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仅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结果支持假设 2b,即增加女性的关系权力会降低男性的工资,并表明在公司和工作层面男性工资向女性重新分配。图1以图形方式显示了女性关系权力不同点的预测边际效应,强调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资的增加和男性工资的下降相关。脚注8
按资格级别重新分配
表3按资格级别报告剥削情况。第 (1) 和 (2) 列显示,对于资质较低的工人,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人的较高工资相关(第 1 列和第 2 列)表3)。对于素质较高的工人,我发现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 3 列和第 4 列)表3)。高素质女性的关系权力系数比低素质女性的关系权力系数低 40% 左右,并且这两个系数之间的差异对于公司内部和工作内部估计具有统计显着性(附录表 A6)。因此,我找到了支持假设 2c 的证据,即女性关系权力对低素质女性工资的影响比对高素质女性的影响更大。
对于资质较低的男性工人,我发现男性工资与女性关系权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第 3 列和第 4 列,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在公司层面上显着性为 0.1%,在工作层面上显着性为 5%。高素质男性的工资与女性关系权力无关,低素质男性和高素质男性的系数之间的差异对于工作内部估计具有统计显着性,但对于公司内部估计则不显着(附录表 A6)。因此,我找到了支持假设 2d 的部分证据,即女性关系权力对低素质男性工资的影响大于对高素质男性工资的影响。总之,我发现女性关系权力对资质较低的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影响更大。此外,
敏感性分析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采用了三种敏感性分析。首先,我汇总第一和第二管理级别来衡量女性关系权力。我发现,根据第二级管理层的代表性,女性关系权力与女性工资之间存在特别密切的关联(附录表 A7)。女性关系权力与男性工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仅限于第二级管理层中的女性代表性。这些发现与德国之前的文献一致(Zimmermann引文2022)并强调女性主管对于缩小性别工资不平等的重要性。
其次,德国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因行业而异(Hinz 和 Gartner引文2005)。遵循文献(齐默尔曼引文2022),我估计了完全交互的模型,包括工业部门作为控制变量,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完全交互回归产生与主回归类似的结果(附录图 A3;附录表 A8,第 1 列)。第三,我将工作按照三位数进行分类。在比较同一职业的工人时,更细粒度的职业分类可能会有所帮助。使用 4 位职业代码,我可以区分 540 个职业,而不是使用 3 位职业代码时的 140 个职业。根据非常详细的 4 位职业代码对工作进行分类会产生与 3 位职业代码类似的结果(附录图 A3;附录表 A8,第 2 栏)。因此,职业的衡量不会影响我的结果。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利用 RIT 框架,分析了企业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重要性,以及机会囤积和剥削机制如何解释企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我采用了来自德国的独特的纵向链接的雇主-雇员数据,其中包括与丰富的调查数据相关的行政数据。我分析了机会囤积和利用的机制。
首先,机会囤积假设男性可能更喜欢其他男性从事高薪工作或公司,从而阻止女性进入高薪公司或工作。这种隔离加剧了性别工资不平等。这种机会囤积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例如公司层面(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我发现企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远低于劳动力市场,这可能是企业层面囤积机会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假设 1a 的证据,该假设指出,企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总体上低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通过分析公司和工作层面的性别工资不平等之间的差异,我调查了工作层面的机会囤积(假设 1b)。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比劳动力市场低 14.6%。这种差异可能是工作层面机会囤积的结果。因此,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和工作层面存在机会囤积现象,这与之前的学术研究一致(例如 Penner等人,2013)。 引文2023)。
其次,剥削假设性别工资不平等源于男性利用其关系权力将女性工资重新分配给男性。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女性的关系权力(例如,通过增加女性经理的存在)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关。这些发现是假设 2a 的证据,即女性管理者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女性工资上涨。我证明这个结果可以在公司和工作层面找到。我对 RIT 文献的第一个贡献是调查工作层面的机会囤积的剥削网。虽然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女性经理的存在对女性工资没有影响(例如 Van Hek 和 Van Der Lippe引文2019),之前的大多数研究发现,公司中女性经理的存在会增加女性的工资(例如 Cohen 和 Huffman引文2007年;齐默尔曼引文2022)。
由于组织资源稀缺(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根据 RIT 的说法, 2019 年),女性工资的增长必须伴随着其他群体工资的下降。我找到了支持假设 2b 的证据,即在公司和工作层面,女性管理人员的增加伴随着男性工人的工资损失,尽管男性工人的工资损失仅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着性。此前关于女性管理者和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纵向研究很少,也发现瑞典女性管理者的存在对男性工资产生了负面影响(Hensvik引文2014)和德国(齐默尔曼引文2022)。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详细调查或讨论这一发现。我对文献的第二个贡献是详细调查公司内部的这种重新分配,并分析哪些群体的工资被重新分配。
尽管从理论上讲,对女性的工资再分配可以来自多种来源,但低素质工人由于议价能力较低,尤其应该受到再分配的影响。我的研究结果主要表明公司和工作岗位中从低素质男性工人到低素质女性工人的重新分配。高素质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的工资受到女性关系权力的影响不如低素质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工资那么强烈,这支持了假设2c和2d。值得注意的是,高素质男性的工资不受女性关系权力的影响。
我的再分配结果与研究一致,因为之前的证据主要表明从关系权力较小的工人到关系权力较多的工人的再分配(Tomaskovic-Devey 和 Avent-Holt)引文2019)。例如,坂本和金(引文2010)发现,男性和有资格的工人的工资高于其对生产力贡献的估计,而女性和无资格工人的工资低于其对生产力的贡献。施韦克和格罗斯(引文2017)表明,在德国,工资分配下半部分的奖金支付减少,而工资分配上半部分的奖金支付增加。我只发现低素质男性在统计上存在显着的负面工资影响,这与工资分布底部工人的工资下降是一致的。
我的研究强调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发现,即女性管理者数量的增加。虽然女性的工资总体上受益于女性经理的存在,但公司内资质较低的男性的工资却下降了。因此,企业内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缩小,但低素质男性和高素质男性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这一发现令人担忧,因为工资不平等总体上一直在加剧(Schweiker 和 Groß引文2017年;托马斯科维奇-德维和新安怡-霍尔特引文2019),而女性管理者的存在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其副作用是加剧男性之间的工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可以尝试增加低素质工人的关系力量,以抵消男性工资不平等的增加,例如,通过增加集体协议的普及程度。
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在公司和工作层面衡量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由于我无法观察个人的公司变化,因此我无法包括工人的固定效应。因此,我无法就对个人工资的影响发表声明。亨斯维克(引文2014)利用工人固定效应发现女性管理者对男性工资的负面影响,表明男性工人个体的工资损失。其次,我不能排除女性潜在工资增长的其他来源,例如公司的收入增长可以大部分分配给女性工资。第三,新出现的文献表明,由于使用交互效应的内部和之间方差,带有交互效应的固定效应回归可能会出现偏差(Giesselmann 和 Schmidt-Catran)引文2022)。由于我的面板只有四个周期长,因此我不能使用仅依赖于方差内的估计器。未来研究的一个途径是使用涵盖更多时间段的面板数据来考虑这一限制。
第四,我排除了兼职工人,因为数据缺乏有关确切工作时间的信息。在我的样本中,只有不到 5% 的男性从事兼职工作,但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因此,考虑兼职就业对于性别不平等至关重要。德国的横断面研究(包括兼职就业)也发现女性经理的存在与女性员工的较高工资之间存在关联(Abendroth等,2017)。 引文2017),我认为当包括兼职工人时,模式可能相似。